釋奠與祭孔
以「孔子」為軸的「立學」與「立廟」
佛 光 大 學
李 紀 祥
摘 要
「釋奠」本是古禮,主於「學」,此「學」於古或曰「庠、序」、或曰「成均」、或曰「辟雍」,於漢則曰「太學、國學」。其禮以「興學」為主意,故所祭之祭主必與「授業者」有關,故稱「先師」;所學所習又與王業有關,故又祭「先聖」,其祭在「學」中舉行。而「祭孔」的起源則與「彷血緣」的「祭祖」禮有關,故主於「廟」,無論在「宗廟」中還是在「孔廟」中皆然。行「祭禮」於「廟」,則祭主以「示」為主,「示」即「木主」,故後世之「祭孔」,其執禮場所必須在「廟」舉行,其禮意以「死者猶在」為主,所謂「通死生幽明」之「祭如在」也。
「釋奠」主於「學」,「祭孔」主於「廟」,兩者之「祀」與「享」意義皆不同。後世發展出的「廟學合一」制度已是歷經漢魏兩晉的演變始乃成型,而「孔子」又為兩者合一的關鍵!然溯論其初,各有歷史時間與歷史形成,本不相同。其合而為一,肇自漢武;由中央立「學」到其「學」以孔為尊,由「祭孔」到成為國典、以及「祭孔」以「釋奠」禮為主體,必為「孔子」為其主軸其間方能成之;無論是歷朝的中央級祀孔或是地方級州郡學、闕里祀孔,皆然。
關鍵詞:釋奠、祭孔、興學、先師、先聖
釋奠與祭孔
以「孔子」為軸的「立學」與「立廟」
一、序言
「釋奠」禮與「祭孔」禮本是兩個不同的國典禮儀,自兩者之起源性便可考知彼等必先、後有別,蓋非僅成詞原義即有不同,兩者兩相映照與聯繫,更可顯出古今之軸;尤其是在一個歷史時間的關鍵點上,探究何以兩者聯繫竟能古今相繫、又何以能相繫而成垂統?本文即欲就後世幾已成一事、幾已成同義之「釋奠」、「祭孔」兩詞,倒述逆溯以觀其自源起處之分,與夫後世之合以究之。筆者所謂之歷史時刻之關鍵點,所指便是在於「孔子之生」與「孔子之歿」:「祭孔」必定興於「孔子之歿」以後,而「釋奠」則興於「孔子之生」之前,雖然對於「釋奠」起源的確切時間我們現在還不是十分明瞭。從文化垂制中有「學」開始,無論是「授者」抑「受者」、「教者」抑「化者」、「學」都不僅僅是指向一個「學習地點」之所在處而已!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興學」之意,指向「師」、指向「子弟」、指向「王業教化」、指向「尊重傳統」;或是於「學」、於「教」、於「傳」、於「習」,於「聖王之業」、於「師之教化」、於「四方來學」,意義的深刻性遞傳在人類經驗與文化於綿綿不絕之傳遞中,經患、歷困、有頓、有揚,經憂患而更迭興,此之謂「興學」、此之謂「王業」、此又之謂「傳統」!
「釋奠」本是古禮,主於「學」,是故其禮舉行必在後世所謂的「國家級學校」之中,其禮以「學習」為主意,故所祭之祭主必與「授業者」有關,故稱「先師」。先儒所謂的「四代之學」,所指乃是「虞、夏、殷、周」。而「祭孔」的起源則與「彷血緣」的「祭祖」禮有關,故主於「廟」。「祭」於「廟」,則祭主以「示」為主,「示」即「木主」,故「孔廟」之「祭孔」,其執禮場所必在「廟」中,其禮以「死者猶在」為主,「通死生幽明」也。原初的「釋奠」主於「學」,後出的「祭孔」主於「廟」,兩者之「祀」與「享」意義皆不同。後世發展出的「廟學合一」已在魏晉之後,但「孔子」仍是兩者合一的轉關;然則溯論其初,各有歷史時間與歷史原因,本不相同。
有關「釋奠」古禮,今日可見文獻中,最詳且最早的記載當見之於戴聖所編之《小戴禮記》中的〈文王世子〉篇。其他文獻如《禮記.王制》、《周禮》等亦皆有述及「釋奠」之文,然或為論「喪禮」中之「奠禮」,或不若此篇之詳,蓋〈文王世子〉篇中述及「釋奠」古禮與「興學」關係,尤其是祭儀、禮意處實較它篇為詳,故也。
「祭孔」則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孔子地位的提升而逐漸形成的一種以「孔子」為祭主的祭禮:從孔門弟子的私禮推尊、到形成為蔚然之儒家學派的宗師、再到地方性諸侯國的祭孔立廟、最終則是國家級的國學尊孔、國禮祭孔,終而取代釋奠古禮中的「先師」而成為「釋奠之新禮」。
二、「釋奠」古禮中的「先聖」、「先師」
細檢先秦所遺之儒家典籍,言及「釋奠」之文處亦不在少,除《禮記》〈文王世子〉〈王制〉〈學記〉外,尚有《周禮》以及伴隨此等經書而興生之注、疏等,都有「釋奠」之文以及關乎其文的釋義與討論。明代李之藻在其《頖宮禮樂疏》之〈釋奠詁〉一文中,便曾就這些儒家典籍中所出現的「釋奠」詞意,作出歸納,其文云:
古者釋奠施於山川、廟社,或施於學。[1]
是李之藻以為「釋奠」之源非僅施於「學」也,亦可祭於山川廟社之典中。其又續云:
釋奠於學,有常時之奠四,……有非時之奠三。[2]
其所謂「常時之奠」者,蓋以〈文王世子〉篇及漢儒鄭玄所注為據,以為「春、秋、冬」與「夏」皆有祀,是謂「常奠」、「時奠」。後者之「非時之奠」,則指「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告訊」。又謂:
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3]
此則欲言文獻所載初始「釋奠」之內容所含性。案、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問世以來世以為名著,故其〈釋奠詁〉先考其詞之源、繼云其內容。其論源處蓋以為「釋奠」之禮施域甚廣,此則誠是,然筆者謂:一則「釋奠」之為古禮,其起源如何吾人已確實確切難考;貳則筆者在此係以後世施於「文廟/祭孔」之「釋奠新禮」為中心,而作出倒述式之逆溯兩者之分、合,是故言「釋奠」,必自其施於「學」處言起,夫以其所以重要,正是在於此處而又遞傳於後世時與「祭孔」相合,故也。
「釋奠」之禮是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存在的官方興學之祭禮,為了興學而有春、秋冬兩次或三次的行禮舉行,這意謂著古時的興學是兩個學期或三個學期制的;也因此在開學/興學時舉行對「先師」的行禮行祭,在古文獻記載中我們已不知道其所祭的「先師」為何人?但因此我們可以確認「釋奠」的原意本是一種「祭師禮」的屬性,並不是「祭孔禮」,本來與「祭孔」無關。《禮記》中的〈文王世子〉篇中記載了孔門對於「學」與「釋奠」及「先師」的「祭典」關係,云: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始立學」顯然是較為隆重的,貴族的子弟入學的始年,舉行「始立學」之禮,不但要舉行「釋奠」之禮於「先師」,對於「先聖」也要一併舉行。「先聖」便是該個年代或該個朝代時的歷史之「古代聖王」或是「開國始王」;而對「先師」的「釋奠」則是在「始立學」之外,尚須於每年或每歲的春時舉行,「秋冬亦如之」。從〈文王世子〉篇中,我們無法得知其所云之「學時之制」其詳為何?但可以知道,有關「釋奠」與「學」的關係,其禮是以「師」為常設受禮的對象。「始立學」之禮的「先聖」,則主要是傳達了「先師」所繫時代與所承垂統的「先聖」,「聖」與「師」之間,有何種文化之軸便設何種「學」,而有何「學」便有何種「設教」,是故此「學」此「教」,必來自於某一個垂統的「先聖」所佈之政,欲以化民,遂有「師」業可言。故《文獻通考》引述漢代之詔文即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4]此義頗以「博士」為古之「師」義,所傳所述則在「傳先王之業」,則「先聖垂統」之義又明矣;「太學」則居於朝廷之中,向於四方所治之天下「流布教化」。漢之「太學」,於古或曰「庠、序」、或曰「成均」、亦曰「辟雍」。《禮記》〈王制〉篇記云: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所謂「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鄭玄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又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再云「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所謂「四代學制」者,即指「虞、夏、殷、周」而言,此蓋漢儒言周代之制時的用語,以「四代」言其因革與傳承,故鄭玄即以「四代相變」為其注文。《文獻通考》馬端臨「案」語云: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5]
又曰:
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6]
案、以上所述,實可略察知《禮記》〈文王世子〉篇追述周制「學禮」中之「師」、「聖」義,於禮意中為何之源,漢人所認知中的「古之立太學」,其「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或可以明「師教」之業與夫其意義為何;而「將以傳先王之業」者,已指向何以「釋奠」禮中須祭「先聖」之故,蓋「先聖」即「先王」也,不曰「王」而曰「聖」,前代、後代相因「垂統」之義尤深!
三、「祭孔」的起源與演變
(一)早期的「祭孔」非國典與「釋奠」禮不同
最初的「祭孔」,只能出現在孔子死後的「孔府」之中,因著「血緣性」的子孫之祭才能以「孔子」為「主」而行「祭孔」,這樣的「祭孔」必定與「祭師」無關,也必定與興學的學校「祭師」無關,故而最初的「祭孔」必定與「釋奠」無關。
「孔廟」的文化意義如果自孔子的「死後」來作源起論述,應當是自孔門諸弟子的服心喪三年及子貢築廬守墓事件作為其起源,而不當如過去學界的論述成習:從魯哀公弔孔誄文或是以漢高祖在魯太牢祭孔,作為言孔廟史的起源,此種編年與紀事本末,其「義」略可以商榷![7]魯哀公之以誄文弔孔子,其實乃是一君臣間事耳,《左傳》中之「傳文」載此事,《禮記》中的〈檀弓〉篇上記有此事,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中亦記載此事,文略不同而所記則類近。魯哀公之弔文,亦僅是「孔府」之家喪禮舉行時出現的君弔臣之誄文,完全無後世所謂「祭孔」之「祭禮」的「事」與「儀」出現。魯哀公之誄孔丘文之事,《左傳》、《史記》、《禮記》皆有記載,三文本中當以《左傳》所記為最早。《左傳》哀公十六年《經》文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文: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旻)天不弔,不慦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所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失志為昏,失所為□。』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禮記˙檀弓》篇上則記云: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史記˙孔子世家》載云:
哀公誄之曰:「昊(旻)天不弔,不慦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失志為昏,失所為□。』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三文本所記略異,其中值得關注的一處記異,為由「師門╱孔門」之視角發出的子貢之言中對哀公「余一人」之譏諷批評,則很明顯的係由《左傳》發端,司馬遷《史記》則承《左傳》而載錄。此處係《左傳》「續經」經文之終,則不論是「續經文」抑或是「解續經之傳文」,至少都是應在「孔丘卒」之後方得為記,也就是說,至少應當是在「孔門」形成之後的敘事之成文。在此敘事成文中,子貢的批評焦點不僅在於哀公之自稱「余一人」的非名,更在於「生不能用,死而誄之」是一「非禮」的事件!而且子貢係引用「夫子之言」來作判定的準則,在此敘事文中,子貢是稱孔子為「夫子」的,《左傳》、《禮記》、《史記》三文本皆同!
案、《春秋》經文、《左氏》傳文皆書曰「卒」,依周制,「大夫曰卒」,故《春秋》書「卒」;然「哀公誄之曰」者,乃魯哀公以諸侯之尊,「誄文」弔其「臣下」耳!我人作為閱讀者,實不能以此而謂哀公之「誄」為「尊孔」特舉也。然則子貢之諷蓋有其所以諷焉,以其對孔子之認知,「生不能用」,自是有慨有傷;是故諷哀公之自稱「余一人」。中國之用孔子、崇孔子、超於「大夫」之位階,實在漢以後事也,漢世以降,「太學」中之「學」、「孔廟」中之「祭」,皆如是!此正與子貢「生不能用」一詞之慨形成一對照,蓋尊與崇中所蘊之慨、憾也。
要之,在人「由生至死」、「由將死至死後」的喪、葬、祭禮之流程中,惟「祭」方屬於召喚死者之「生前」入於「祭者」之當下仍活著的生命之事,因而「受祭者」與「祭者」之前也才能形成兩者間--「此生╱祭者╱活者之現在」與「彼生╱受祭者╱死者之生前」--的「共在」世界。後世所謂的成為國典之「祭孔」,其義當在此。因此,孔門中尚無「祭師」之事出現!「孔子」與「異姓祭孔」形成的關鍵,在於孔子死後,「孔門諸弟子」對其所尊敬的「夫子」,作出敬意與情意的表示,因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獻所見第一次弟子對老師行「心喪三年」的「彷血緣性喪禮」!「三年」意謂了彷血緣性中「父子」義的引入「師生」情中;而「心喪」一詞,更見出孔門諸弟子有意「以師比父」,從血緣性的角度出發來模仿其「三年居喪」之禮以表達其情,這是非血緣的異性之仿血緣之舉動;所以行與所以彷,在其師生之情,其行禮之源係緣於此。這樣的舉動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尚係第一次出現:由「非血緣性」的「諸生」而「彷」其「血緣性」的「子弟」,「孔門諸生」雖未「與祭」,來而卻「服心喪三年」一如孔宅諸子、弟,則未知當時的「孔氏族人」與鄉里之人視此為何?總之,文獻中所出現的「非血緣性」的「與喪之禮」,可以稱之為中國或是東亞更或者是世界史上的「首次事件」,一次被記錄下來的有意義的「歷史事件」,由於這次事件,方纔開啟了後世「祭孔」的地方禮、國典、釋奠新禮的先河。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文云: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適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諸弟子之服「心喪」與子貢(贛)的結廬守墓,雖在「墓畔」,是屬「死後」之「喪」事,尚無「與祭」其師的「祭」禮之事。觀乎司馬遷之行文中,諸弟子之「與喪」無不出自於師生間之至情以及對老師的不捨!在司馬遷筆下,除了「高皇帝適魯」以太牢「祠焉」外,其餘均為「先謁然後從政」的「諸侯卿相」,更重要的,係彼等皆於「魯地」祠、謁,未聞中央朝廷有關「祠孔」的記載。
其次,堪值得注意者,為弟子守喪之文中出現了的「三年」與「心喪」之詞。「三年」乃是模仿子女為父母守喪的血緣性之禮而來,是諸弟子視孔子若父也;而「心喪」一詞,蓋其所意在於欲表述諸弟子未如孔氏子孫之必須著「喪服」也,既未服喪服,故曰「心喪」,正以「心」之內詞相對於以「服」為顯外之外詞也。如此,則司馬遷此處之行文猶有不清處,前曰「弟子皆服三年」、後曰「三年心喪畢」,前句之「服」惟有從後句而解為「心喪之服╱服心喪」方可通。此若與《禮記˙檀弓》篇參看,則其意便極為明顯,蓋司馬遷本文多自〈檀弓〉採擷也。《禮記˙檀弓》記載云: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此一「若」字開啟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師生」與「父子」間的非血緣與血緣的相彷關係。注意〈檀弓〉篇中所云皆為「喪」,是諸弟子所論皆在「喪事」階段也。而諸弟子之討論「如何與喪」正是其所討論之重點,由其所討論看來,可見這是一件「前所無之」的事件,即便是在彼等追隨孔子期間,也是一個從未討論過的議題之首次出現:首次出現恰恰與孔子之死與孔子之喪有關;因此,子貢藉由孔子喪顏回、喪子路「若子而無服」來作為參照,提出了「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的觀點與作法,便獲得眾弟子的同意而成為後來在司馬遷筆下的史實敘事之文。但在〈檀弓〉篇中,我們讀到的確切文字卻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細心的讀者可以察見此中並無一「師」字的出現,諸弟子對孔子的服喪也僅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夫子」一詞決不能等同於「師」!同時,在「周天子」之制下,已有「釋奠」古禮中的「先師」之禮,且為階屬於國家祭典層級的「師」,則孔門弟子們便不可能以「祭師之禮」來為孔子舉行禮儀來表達其哀情與敬意;如果可以對孔子舉行「祭師」之「釋奠」,弟子們早就做了,可見弟子們的意見最後落實於「喪夫子若喪父」而終止於為孔子「行喪禮」,而不能為其舉行「彷國典」之「釋奠祭禮」,不是沒有原因與歷史背景的!
在〈檀弓〉篇、〈孔子世家〉中,雖然只能讀到有關孔子死後如何做法的子貢一家之言,但卻可以想見:當時必有各種意見,甚至可能包括主張應當「若服父喪」意見的提出者。正是因為由後視前,對孔門諸弟子而言,孔子之死與孔子之喪為一獨一無二的大事件,因此也惟有在「孔子死後」而非在「孔子生時」才有可能出現「祭孔」與「孔廟」的歷代之禮的傳統之出現與形成,可以想見,「祭孔╱孔廟」傳統的起源必在孔子死後,〈檀弓〉與《史記》〈孔子世家〉的行文記敘,便正好見證了孔門之第一代的諸弟子與孔子之情誼如何,以及由情誼若父子而來的「喪夫子若喪父,無服」的傳統之起源,正是起源於諸弟子的討論聚會與子貢意見的成為共識之意義。要之,魯哀公的誄文只是國君對大夫之顯者的弔辭,並不是後世「祭孔╱孔廟」的起源。凡將魯哀公之弔文納入「孔廟起源之史」的「起源之域」中者,恐怕不僅是對於「祭孔」、「孔廟」的本質有所誤解,領會未透,同時也是解錯了方向![8]
從諸弟子的心喪三年到子貢的守墓,為「異姓之祭」注入了「師生」模式的新的內容,這在歷史上乃是一件大事,而由孔門弟子之「緣情行禮」而來,雖未成「制」,亦未與於「祭」;要之,連孔子都僅是對周公以「夢」為喻;但以異姓之後人對於前人之緣情的表答情意,卻在孔子死後由孔門弟子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首度異姓模式的「師生之間」,因模仿「祖孫」的同姓模式,而出現了一種「文化傳承」的意義,這個「文化傳承」的內含,是「非血緣性」的。雖則「守墓」,在祭祖儀式之禮意上僅屬於「葬禮」,是子孫表其哀的「凶禮」;尚未能提升至於一種文化傳承性的位階,這種位階,必須要從「祭禮」的角度、內含與層次纔能看出「祭孔」之「如」其所仿的「祭祖」之大意義,也就是從文化角度成立了「傳承」的意義,非血緣性與血緣性並行,血緣與文化並行,乃有其文明可言,所謂國家或是家國的詞彙也纔有了意含。
總之,在孔子初歿之際的孔門服喪事件,意謂著此時的「尊孔」尚未以「師」的名義來「祭孔」,因為,在周天子與諸侯之四時學祭中的「師」乃是古禮中的「師」,與孔子無關。
原初的釋奠之禮仍然是周天子的釋奠之禮,只能與周家的「先聖」、「先師」有關,與早期的「服孔喪」之禮無關(不論是魯儒的祭孔還是孔氏的家祭)。《禮記》〈王制〉篇記曰: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注云:
禡,師祭也。
〈王制〉又載: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鄭玄注「受命於祖」為「告祖也」,注「學」為「定兵謀也」;注「釋奠」則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故知此「學」與天子征伐主兵之學有關,是「學」為「主兵」之學也。亦知鄭玄訓解「釋奠」為「釋菜奠幣」。「受命於祖」與「受成於學」對言,殊有意義,正與「廟」、「學」分途有關。是故惟孔子出,方有所謂「廟學合一」之「釋奠/祀孔」,在「祭孔之禮」中,「釋奠」又較諸「釋菜」為隆,蓋後者無「奠幣」故也。
在《禮記疏》中,彙集了許多漢及魏晉時先儒的「釋奠」觀點,有些以為「釋奠」是「禮先師」之禮,與「祭」無關;有些則以為「釋奠」即是「祭先師、先聖」,仍是「祭」也;不論「主祭」或是「主禮」,都反映了「釋奠」的原初禮意,仍自「告廟」而出,尤其是天子出兵、返師的「告廟」,是故「釋奠」仍與「祖禰」有關,《周禮》所云「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即是此義,《周禮注疏》中載《疏》云:
釋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巳。七廟俱告,故祖禰并言。
這乃是早期「釋奠」的「主兵」之屬性,既然「主兵」,則「師」為彼師而非此師之義;「主兵」意義下的「釋奠」,其「先聖」意含當自血緣性之源來體會,這是「釋奠」禮中「宗廟」制下的祖源性,《史記》的〈五帝本紀〉最能反映此點。《周禮疏》疏文中所云之「非時而祭」,蓋以「奠」為「凶禮」也,是故於天子征事中必有亡傷,傷而亡則服喪禮,故必曰「非時」,凡祖禰之亡不能預知,故其喪事不能「時」,故曰「奠」,《疏》之文云「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當是此意!至於「釋奠」的「主文」屬性,應是在於天子的「興學」與「立教」之面,〈文王世子〉篇最能反映此一屬性,「先師」已脫離「祖禰」的「告廟」儀典,由「主兵」而轉向「主文」,同時「釋奠」亦改在「學校」中舉行,是故鄭玄注以為「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即是此義下的推論。然鄭玄以宗法封建崩後之兩漢背景來推論〈文王世子〉中的周代「先師」,雖其意義無差,或恐與事實有違,蓋平民在周代初年必不能為天子興學之「先師」,凡可以於亡後參預於周王室中央學校成為「釋奠」、「釋菜」禮中的「先師」者,即令不與天子同宗,亦必為百官貴族也。
四、「祭孔」的演變:孔子為「先師/聖」與「釋奠」新禮
孔子有廟,依「血緣性」之文化傳統,必在孔子歿後;又孔子有廟,受異姓之祭,則源自孔門「彷血緣性」而啟之;異性「孔廟」逐漸自魯地曲阜而上昇其地位,遂終於後世王朝遞變中於中央首都之中為孔子興立「孔廟」,此是「祭孔」成為「國典」的關鍵。然「祭孔」成為國典,必基於、亦端視歷代帝王之在何種程度與等級上推尊與尊崇孔子之儒學而定。孔子之後,推尊儒學成為國家級之學者,首自漢朝始,而漢世之「尊孔」,多以「立學」、「隆儒」、「傳經」為主,此遂啟漢世於中央立太學、地方立州郡學,以及專隆六藝傳經之諸博士,遂開兩漢儒林傳經之譜。案、漢武時從董仲舒對策議獨尊儒術、又從公孫弘議設博士弟子員,論者謂漢武之時實為漢世設太學興學校之始。故班固〈漢書儒林傳贊〉云: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
〈漢書董仲舒傳〉亦記云: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又云: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所記,皆以漢代中央太學之設立,實始自武帝也。又以其首議及其議建之功,歸於董仲舒。是《漢書》中的觀點及其史述,所謂中央興太學,其內容既自仲舒發之,則所謂「以養天下士」與夫由「置明師」而養之者,其「師」所授、其「士」所受之內容,皆在孔子所傳述之六藝經學,亦即所謂「儒學」。故漢代尊孔,實集中於「興學」與「立學」一面,武帝所立學校之官,以及置「博士弟子員」之「弟子」,「太學」、「明師」、「弟子」,已經將孔子置於核心位所而環繞出一個新朝代中的「新學」矣,而此「新學」,實以「孔子」為核心而成。
又《漢書》〈循吏傳〉云:
至武帝時,乃立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此一史述則係記載了漢初迄漢武之時的地方性郡國亦興立學校之實。
因此,「孔子」之進入中央京師與成為國家級典禮的「釋奠」中,其前提與要件,仍在於一個時代必須先有帝王倡議「興學」之舉。是故漢、魏、晉之世代,必先有中央朝廷之「興學」,立「太學」、「辟雍」,而後方得有於太學中舉行「釋奠」以祭「先師」,若受祀之「先師」者為「孔子」時,則「釋奠」之新禮可謂已以「孔學」為中心下的「釋奠/祭孔」,此時的國家級之興學釋奠與祭祀先師孔子已合而為一,所謂的以「祭孔」為中心向「先師」致意之「釋奠新禮」乃在歷史中逐漸形成。
論者又有所謂「廟學合一之制」始於魏晉之時者,則此謂中央立「學」,「太學」中所學、習皆以「孔子之學」為主軸;而為尊孔,又於「太學」中立廟,此「廟」為主於異姓祭之「孔廟」;則於文化空間上,「廟學」成矣!「學」為「太學」,主於「釋奠」;「廟」則為「祭孔」;此後在「廟學合一」制下,「釋奠」與「廟祭」合一,「釋奠」即「祭孔」、「祭孔」即「釋奠」,無論在其「禮」、其「樂」、其「舞」上皆然!觀蘇良嗣〈《文廟祀典考》後序〉云:
曩時學與廟異,故釋奠在學、享祀在廟,捷然不同。考之西漢之祀孔子,只在魯廟;而東漢行釋菜、釋奠之禮,則皆在國學。
「釋奠在學、享祀在廟」已明確地道出其原初所以分之義![9]
在漢人的歷史認知中,皆以漢世帝王之興學,係始於漢文、漢武兩帝之時。而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從公孫弘之議設博士弟子員以向博士學經,而「經」又係孔子所傳、所述、所訂、所作,是故漢武帝尤為此下歷史認知中的關鍵人物,成為「秦火毀學」之後的「興學」之第一帝;彼所興學舉措,即是以「孔子所傳之學」為其中心,《史記》與《漢書》中的〈儒林(列)傳〉便係反映此一歷史認知的最佳實錄!
《後漢書》中所敘寫的後漢時代對前漢興學之記載,最可反映漢世興學的歷史流傳與認知中的形塑為何!〈朱浮傳〉中記載後漢光武帝開國時興學事云:
建武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
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所謂「國學既興」者,乃指漢光武帝於建武五年修建「太學」之事。〈儒林傳〉載云:
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中。
同書〈桓榮傳〉又載:
建武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
同書〈翟酺傳〉更云其所認知之漢世興學史事,云: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
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
可見無論是興太學舍、還是辟雍,皆是中央君臣在共同的認知之下,以「孔子所傳之學」為核心的「興學」之舉。然或稱太學、或稱辟雍,皆同可稱其學為「國學」也,此時之「國學」已是以「孔子」為中心的興學立校之國家級舉措。但在此興學舉措中,我們並未見到「祀孔」典禮的孔聖廟制出現在中央的「國學」之中。研究中國教育史或是中國孔廟史的學者們,之所以會特重魏晉時代的「廟學合一」之制,不論是前學後廟、還是左學右廟,便是在此一「學」、「廟」尚未合一的歷史背景之下對此一現象的關注與研究。亦因此,有關劉邦稱帝後適魯以太牢三牲之禮對孔子的「祀典」,此一歷史事件在「祭孔/釋奠」之史中應當如何定位,恐怕便不能單以「太牢」禮來為劉邦之尊儒崇孔作出「第一位祀孔的帝王」之說法;劉邦祀孔顯與後世在「太學」及「闕里」之興學祀孔的意義大不同!要之,在「孔子」地位的上升歷史過程中,「秦火」之後的兩漢時期,多在中央太學中反映出「孔子」與「學」的結合性,故東漢諸帝多幸太學宣講經學,親幸魯地闕里以「祭孔」者則少。而魏晉與隋唐時期,則多反映出「孔子」與「廟祭」在中央合一的情形,無論是太子祭孔、或是天子親自與祭,都顯示出「孔子」被歷代諸帝視為「施教天下」中不可忽略的一位歷史人物,因而便不止是「興學」中的「傳述」孔子之學,而更是於中央「立廟」來「祭孔」!「祭孔」以尊與「述孔」以傳學,不外乎都是為了要以孔子所傳的「六藝/六經」之學,教化天下,同時亦自此中來取士。因此,古昔施於天子宗廟與四時祭享的太牢之禮、六代之樂、八佾之舞,或是廟祭時的初、亞、終三獻之序禮,便逐漸由皇室的血緣性場域向非血緣性場域移動。隋代及唐初的以「周公、孔子」為「先聖」、「先師」,或是以「孔子、顏回」為「先聖」、「先師」,便已反映出此點,〈文王世子〉篇中我們不能知其姓氏的周家「先聖」、「先師」,在此已因「孔子」而有了明確性:不論是「以孔為聖」還是「以孔為師」,「孔子」都已是歷代的「教化之宗主」,與歷代帝王的血緣性與否無關,「興學立教」的「祭孔國典」與主祭者的血緣性與否無關:主祭者無論是天子、太子、博士、太常之長,其「與祭」乃是為了「興學立教」,而非「祖禰」!以是,在此一原為宗廟中所施之太牢、八佾禮樂舞器移向「祭孔」典禮的歷史形成中,遂出現了齊武帝時主司「祭孔」的單位所提的問題:究竟「祭孔」之禮應當為「釋奠」抑「釋菜」?究竟「祭孔」當「行何禮」?「用何樂」?「置何器」?鄭樵《通志》轉載此事,云: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
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通志》又載云:
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令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
《南齊書》〈禮志〉則載: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此一記載,正足以反映出兩漢時期的「新學」之「興學」,乃是「以孔為尊」式的博士傳經之學,前、後《漢書》中的〈儒林傳〉便係以「諸經授受」來載錄「師」與「弟子」間的聯繫。而魏晉以下迄於隋唐,則是「孔廟」進入中央廟堂之上,成為「異姓所宗」而受祀受享,此乃緣於「師─弟子」之間的可依「彷血緣」的祭享聯繫。在此一異姓「廟祭」中,無論是天子、太子、有司、諸來學者,都是在「弟子」的位所上行「尊師禮」於「祭典」之中;且其討論的層次有愈後愈高的情形出現,尤其是對於「孔子」的位所,無論是師還是聖,都已無礙於其地位的形成,於「師」,則「不當臣之」,於「聖」,則「比擬帝王」;上引記載中的「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便反映出對「孔聖」、「孔師」的討論,乃是在於「為天下所宗」、「為傳承所宗」之位所層級上的聚焦議論。
在《晉書》〈禮志〉中,其記載回溯了始於三國時魏正始中的「釋奠」之禮進入「祭孔」,並且是於中央之「學」中廟祭的歷史敘述,文載云:
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
在此敘述中,「釋奠」禮係由「太常」主司,祭於「辟雍」,《晉書》且特云齊王「弗躬親」,意在為其下文作出晉時成帝、穆帝、孝武帝等諸帝之「親釋奠」的特殊與隆重,《晉書》〈禮志〉述云:
及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晉書》〈禮志〉又載: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意義仍然相同,皆在強調晉帝為太子時「親釋奠」的殊勝處,末句所述之「權以中堂為太學」者,則顯示出「廟、學初合」之時的場所之不穩定性,可見雖有「故事」,仍未成為「常制」也。而晉元帝時之以「顏回配享孔子」,仍然是以「宗廟」的血緣性之制度來摹擬非血緣性屬性的「師-生」表徵,表徵「孔-顏」關係的方式,在「釋奠」禮的儀式中,仍然是自宗廟禮制中「配享」之「彷」而來。
《晉書》中〈潘尼傳〉中所錄潘尼所撰作的〈釋奠頌〉,尤為「孔廟史」上的一篇特殊文章,《晉書》本傳中載錄全文,云:
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辯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有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般辟俛仰,可以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下略)
案、此一「釋奠祭典」在過去實無禮、無樂、無器、無舞可遵循,則南朝時代的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之奏,正足反映此一「禮」、「器」、「樂」、「舞」在制度上懸乏闕如的現象。是故《宋書》〈禮志〉中所載「釋奠」禮之「服冕之制」者,正是此一「闕如」之中的「制作」歷程,《宋書》中對此一歷程作出史述之載,云:
周監二代,典制詳密,故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嘉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囗囗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至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至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袞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略之。晉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天冠也。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纓,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韍也。絳,絳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裙,絳緣中衣,絳,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裙,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單衣。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儀:「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表:「不應素幘。」詔門下詳議,帝執宜如舊,遂不改。
此處討論「釋奠先聖」的「冠冕禮服」,正見禮、樂、舞、器、衣冠等的「釋奠新禮」是如何地在歷史之中的形成與發展,且係以「孔子」為中心。職是,我們也可以說:如果孔子歿後,孔門諸弟子的「服喪若父」是以「彷血緣禮」來向其「師」致敬,那麼,後代帝王行於中央的「釋奠/祭孔」之禮,又何嘗不是自血緣性的宗廟、四時祭享中取用了其禮、其樂、其器來祭祀異姓的「孔子」呢!則「孔子為聖」與「孔子為師」,就是一個格局上與視域上的「天子立教」之職與責,而不是孔子可以分身為二,移動在聖、師之間,就孔子而言,聖與師,猶如「若聖與仁」,皆是一事耳!
結 語
近代以來,東亞諸國受到西方的影響,學校制度於是仿自歐洲為其原型,係以小學、中學、大學為模式;從某一個角度來說,這樣的模式基本精神仍然是「流化於天下」式的,所謂「國學」、「私學」都是為了教育的「普及」,使人人皆得而入「學」受「教」;這樣的「興學」精神,其實與東亞地區傳統學制中太學(國學)、州學、郡學、府學與縣學、鄉校等廣學的教化精神,在模式上並沒有甚麼太大的不同,都是一種層級制的普設學校模式;差異的重點要義,還在於東亞傳統的學制中,有其明確的「何為學」、「學為何」之宗旨:以古聖先師所傳習的文本、以古人智慧的結晶作為傳統,並且立於現在、尊重傳統、前瞻將來。下一代在受教的目標上是明確的,傳、承之間有如長河不絕,對於文化斷裂性的克服顯然有其思考與努力的明確方向。若將「釋奠古禮」放在「釋奠新儀」的歷史角度重新觀察,則顯現在歷史長河中的當時人在各自當下的努力,尤其是對「新禮新儀」的努力,確實有其「制禮作樂」的主軸與文化意義在其間;此一主軸中的「師」、「聖」與「學」,較諸於近代模式下西式學制之「校訓」提揭也者,表相上看來似乎相近相類,然而論其深度與意義感受,卻大有不同;在今日學制中,固然在每一個學期之初的開學儀式中也有「勉學」的儀式,但若與古代的「釋奠」之禮相較,顯然對比出的異趣足可令我們深深反省,為何虔誠不再了,甚麼樣的禮儀符號與場域能再度作為一種磁場中心,將授者、受者、學者、習者、家長、立學主政者的用心幅湊環聚成為一個「人在生生世界之中」的成長與成熟之意義世界呢?孔子究竟在甚麼位所上向我們言傳了甚麼呢?為甚麼是「人能弘道」?一種儒家式的「人倫常道」何以經由「文化體」位所的「師」之「教化」,便能啟迪「人」返歸到「人之為人」的生命自身?總之,「孔子」與「諸弟子」的關係,乃是一「非血緣性」的傳道、明道、學習、授受的關係,孔子「有教無類」已蘊「教化天下」之義,四方弟子來學,亦正顯示「人之性」中有著一種「誠之明之」的蛹動而不能已,「自行束脩」反映的正是「師-弟」之間的所為、所求,開啟了的便是「道」的「生生」已在「孔子」身上開啟了文化之軸。凡是為「聖」為「王」者,想要開啟一個「常道立學」的時代,則有關如何對待「師」的思考,便是一時代主政者必將面對者,無論是「先師」、「後師」、還是「師-弟子」間的傳傳承承,「人之為人」的意義不論是在過去、於現在、還是在將來,一貫之軸的常道所在,常在變易中考驗著知識份子與讀書士人,猶如沈約在其《宋書》〈禮志〉中所致之感慨:
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宜。
儘管歷史中的變化常大到令我們深崁其中而辛苦經營,通古今之宜以面對其斷裂,但觀諸《論語》中曾子所云者: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10]
亦足令人興發。曾子所云,即是孔子居「夫子」位所而「教/授」:「仁以為己任」,此「仁」此「己」,於是乎透過孔子此「師」,「學」者可以在「習」中知「道」之在「己」!於是曾子,作為孔子的弟子,其感悟的生命體悟以及慨然承擔的使命意識,便顯示了由其「師」而來的「教化」之影響,在「師-弟」的「授受」與「傳承」中,「師道」的義意也即是「明道」與「教化」的意義,便在「人倫」的代代不絕中,成為「文化之軸」。生生流轉之常,必「待有人」明之者,孔子已在文化之軸的位所上開啟了孔門的「師道」亦隨之流轉,向於能常矣;從「釋奠在學、享祀在廟」到「廟、學合一」,「釋奠」的古禮與新儀,也曾在歷史的變遷中因著「孔子」而流轉了古今之義;那麼,在這樣的古今映照之下,我們這一輩對於傳統興學、立學時向「先師」、「先聖」致敬的「釋奠」禮儀,能不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呢!特別是在這東風、西風交替的時刻。
[1]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明萬曆間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卷三,頁358。
[2]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三,頁358。
[3]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卷三,頁358-9。
[4]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卷40,學校一,頁383。
[5]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0,頁379。
[6] 同上註引。
[7] 如明李之藻的《頖宮禮樂疏》(明萬曆間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卷一之〈歷代褒崇疏〉,以「編年」體裁形式,將歷朝以來對孔子褒崇祭祀等事件依次繫之,備覽觀要;惟此〈疏〉首條所繫,歸之於漢高,云:「漢高皇帝十二年,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頁92),則恐未能明「褒崇孔子」諦義也。
[8] 是故今傳題為宋本之孔傳《東家雜記》(愛日精盧影宋本,濟南:孔子文化大全,山東友誼書社,1990.9)於〈歷代崇祀〉首條即記:「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百戶。」(卷上,葉六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以為孔子逝去第二年(十七年)魯哀公便「仍舊宅立廟,守塋廟以百戶。」此皆非也。又或是追隨鄭玄的說法,以魯哀公弔文中之「尼父」為國君封諡孔子之始,並以此作為「孔廟」的起源,此亦非也,清龐鍾璐已駁之,見龐鍾璐《文廟祀典考》(台北:中國禮樂學會),〈祀典溯源一〉,頁206-7,龐氏按語。
[9] 蘇良嗣〈文廟禮樂考後序〉,見金之植、宋鋐編,《文廟禮樂考》。
[10] 這也恰好是我的太老師錢穆(賓四)先生在臺灣退出杏壇前,於臺北外雙溪「素書樓」中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上最後一堂課時的開講主題!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釋奠與祭孔
於
晚上9:02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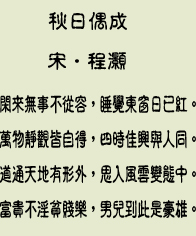
1 意見:
If some one desires expert view on the topic of blogging after that i propose him/her to go
to see this website, Keep up the fastidious job.
Feel free to surf to my page :: landing Page design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