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的形上學議題
-----孔子的「祭如在」與朱子的「祭聖賢之可能」
摘 要
本文嘗試自孔子所言「祭如在」之如何可能的形上提問開始,意圖揭示「祭如在」世界的存在論根源。並以為「如」字的解讀應有兩義:其一,為一種「模仿」義的「如在」世界;其二,為一種「共在」義的「如在」世界。
本文亦自「血緣性」的「宗廟世界」所成立的「祖先—子孫」之聯繫,以討論「非血緣性」的「先聖賢—後學」之關係如何可能尋求出一存在論的根源,此一探尋正是「孔廟世界」與「鄉祠先賢世界」之「祭如在」的如何可能的形上學提問與存在論之回應。也是朱子及其弟子黃榦所面對的新儒學議題。
本文認為,朱子自「理氣論」以尋求對「先賢往聖」能夠「感通」之可能,仍然存有「兩重世界」的特性;而其弟子黃榦的「琴聲之喻論」則繼承了朱子的課題,提出「祭如在」中祭者與受祭者「共在」之可能。朱子及其門人的提問與回應,反映出無論「祭如在」的解釋走向是「模仿性」或「共在性」的模式,儒學的理想與發展主軸,已從「宗廟世界」而轉向「孔廟世界」,前者為後者之基,後者則為前者的人文教化性之躍升。
關鍵詞:孔廟世界 宗廟世界 祭如在 形上學議題
如的模仿義 如的共在義
孔廟的形上學議題
-----孔子的「祭如在」與朱子的「祭聖賢之可能」
一、 孔廟的形上議題之面對與聖賢祭祀之可能性
已故的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均曾為文提問過儒學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即:人死了還能「在」否?又:以何種方式而「在」?對筆者而言,這個議題之所以重要,不僅是一個涉及「儒學文本」之意義的重要課題,抑且也是一個面對「孔廟世界」如何可能的重要課題。
筆者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理學世界中的「歷史」與「存在」>,來迴向於唐君毅先生,[1]唐先生在其《人生之體驗續篇》中,曾提出了這個人生以及儒家的大課題:仰慕先賢究竟有無可能?唐先生問曰:「人死了」究竟能以何種方式繼續「存在」?[2]錢穆先生則是在其《靈魂與心》中提出了這個儒家式的問題:人死後將如何「在」?[3]
這不僅牽涉到我們「活著」的本身對「故人(古人)」、對「已逝的人╱往者」的意義,也更牽涉到「一旦我們不再活著」對「我們活著」有何意義?因此,「歷史」的意義就是:「過去」對「現在」的意義何在?以及:「現在」以何種態度面對「不再╱不在」?
回到孔廟的議題中來,這個形而上的提問,便是:「古聖先賢」對「現在的人」意義何在?為什孔廟中必須進行對「聖賢」的祭祀,以表達「祭如在」的「今古之能共在」及「今人與古人之能相感」者,其存在的根源何在?
「孔廟世界」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一如「歷史世界」般的存在,在我們所熟知的「文本」與「遺物」之歷史樣式之外,以另類樣式--「孔廟」的樣式而存在?還是「孔廟世界」就是一個一如「宗教」般的「神聖殿堂」的存在?如果是後者,那麼「孔廟世界」存在本質的探討,就一如英國神學家保羅˙巴德漢在其著作《不朽還是消亡?》中的探索與提問:「人死後?」。「人之必死」既然是確定的,則「死後生命有無」?「死後存在」是「在此世」抑或有一個「來世」俟其來完成此一「不朽」的生命性,甚或是「復活」與「永生」?[4]巴德漢從「宗教神學」而出發的探問,極有類似於中國古代儒家對於「死生」與「鬼神」、「祖先」的探問!也類似於宋明新儒家以及當代新儒家的探問:「先聖與先賢」的「不朽」是在「此世」還是「後世」!這又回返到民國初年的課題:「儒家是否為宗教?」這個課題在近代以來以及當代的學者及所謂新儒家中,已經作出了許多立場與觀點的表達,特別是康有為、陳漢章等人從「宗教/國教」之立場所提出的「孔教論」,以及熊十力、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自哲學與思想的立場所作的有關於「儒家/儒學」之「宗教性」的近代探索。[5]
本文不打算在「儒家」與「宗教」的「是否」問題上打轉,換言之,源自於西方語境的「宗教」一詞並不構成本文「格義」的中西比較觀,無論是以西為宗之同化或是平行比較之的差異區分的那種五四模式的比較觀點與進路。本文只想對於「孔廟世界」作出一當代的形上提問,使「孔廟世界」在根源的提問下成立一個學術上可以展開並且討論的形上議題與課題,並且藉此一形上議題的成立,去考察與重新思索古人--尤其是朱子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回應。我們將會發現,如果從孔子的「祭如在」出發,那麼對於這個關鍵性的「如」字,思考與回應這個形上學提問的方式大致上有兩種:一種是「相對主義」模式的,一種則是「存在論」式的。
這個問題的首先提出,並追求其根源以期能予孔廟與鄉祠之祭祀先賢以存在之基者,就筆者所知,當屬宋代之朱熹。雖然在孔子自身以及與弟子的問答對話記錄中,已有許多關於祭祀祖先以及古代聖王和祭祀鬼神的言論,但是卻沒有提到有關祭祀「聖賢」的言論。當然這種言論不會在孔子的在世之時被討論,因為「孔廟」與「孔廟祭祀」必是在孔子死後才會出現;並且隨著孔子及其儒學成為文化之主軸與後世歷代儒者與官方之尊崇下所形成的一種歷史現象。然而,無可否認,今日孔廟建置及其祀孔或祀孔後諸賢之種種禮樂儀典,仍然與孔子時所面對的「宗廟」及其祭祀之禮制有關,因此,孔子所談論的許多看法,仍然有其意義。畢竟,「孔廟與祭祀」是自「宗廟與祭祀」轉化而來,從「血緣祭祀」到「非血緣祭祀」,此即以「孔子」與「聖賢」為軸心的歷史文化所產生出的儒學文本與蘊含在「孔廟」中的儒學之聖賢存在觀,其中便有許多新的儒學課題必須面對,很顯然這個面對就是宋代新儒家要對孔子所言的「祭如在」進行重讀與重詮。《國語》中<魯語>云: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師于民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6]
這乃是以血緣為之基礎的「宗廟世界」之祭祀,其祀典只能是同族者,敬宗法祖收族皆在於此。因此,當以「孔子」所代表的聖賢文化傳統自「宗廟世界」轉化而成立了「孔廟世界」時,「孔廟世界」中的「統」乃稱之為「道統」之以「道」為「統」,而非以「血緣」為「宗」為「統」時,勢必要面對的形上追問、質疑的存在論基礎何在便是:「非我族類」的「先賢--後學」之關係,乃是一以「道統」而非以「血統」而成立的「敬」與「可敬」、「祭」與「所祭」的世界,雖然「孝子」行「祭」於「祖先」也是要以「敬」為態度的根本,然而,以「道」為「統」畢竟仍是要面對此一質問,質問其存在的基礎,何在?
雖然在孔子之後,隨著魯國哀公之誄文、漢平帝之封周公後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而漸進於以周公、孔子為國家祀典的先聖與先師,「孔廟」的祭祀傳統逐漸形成,在唐代更正式在各州縣皆立「廟學」,將以「祭祀」為主的「廟」與以「儒學」為主的「學」合而為一,而成國家級的「廟學合一」之制。[7]而其祀典之禮儀、樂舞等儀式,據文獻上的考察,實皆自周代宗廟祭祀制度而來,包括今日猶有爭議的「祭孔」時用的是八佾還是六佾,也都是周代禮制中的祭典舞儀。這反映的是:在祀孔已成為國家級祭典時,孔子的身分是否可以平行於國君,近世以來的「萬世師表」的「師」之位所,是「國」之下還是必須以中國文化中的「師弟傳統」來看待,亦即是已經超越了「國」與「朝代」,爭議的八佾與六佾,仍然是春秋時代的周代宗廟獻祭制度的一環,也是在《春秋》褒貶之文中便已經出現的一個爭議課題。可見「孔廟」雖然產生在「孔子死後」,但其內涵卻與孔子「生前」所面對的「宗廟」有其移轉的密切關係。可以這麼說,睽諸史實,「孔廟」中的「祀孔」與「祀先賢」便是以周代「有血緣」的「宗廟」與「祭祖先」為模擬的藍本。然而,對於「祭孔」與「祭賢」的「非血緣」問題,自春秋以來,從無人問過,也無人去探究過。一直到朱子自己面對了在鄉祠與書院中祭祀孔子與先賢的實際行動之後,「祭孔」與「祭賢」何以可能?成了朱子首先提出的一個形上學之問題與議題。
對於朱子的所以必須追問「祭祀先賢之可能」的議題,自然有其背景。朱子不僅必須繼承北宋伊洛之學的「重接孔-孟」,抑且也必須面對南宋時對於北宋的重新論述,從而面對「周張二程」的面對「孔-孟」之雙重面對。這種雙重的面對使朱子產生了「道統論」的「系譜」,一方面是以「四子書」建構了「孔、曾、思、孟」,一方面則是以《伊洛淵源錄》與《近思錄》建構了「周-張-二程」的「孟後千年之統」。這兩種「統」的建構皆是以「文本」為之。堪注意,「文本」之「統」是以「道」為其內在性,也可以稱為是以「內在基因」來認定「道」的「真傳」,由是而可以進入與建構其「道統」。這種「以道為統」彷彿兩漢時期存於史書論述中的「儒林傳」,重點在「反漢」而置換了新的內涵而稱之為「道學」,是以同為史書的《宋史》便改其傳名稱呼而稱之為〈道學傳〉。仍應賦予注意的是,不論「儒林」還是「道學」,其間的系譜畫線關係均為「師弟」關係。不一定要「親受」,也可以是由與先賢先聖的「文本」之關係來建立關係。
但是,這一套以「文本」為中心的「人與人」--前人、聖賢與後人、學習者的關係建構,在朱子必須要在鄉祠中作出「祭祀」之行為時,遭遇到了「宗廟時代」與「祭祖行為」所不曾面對過的課題:此即是朱子現在所祭祀的是「先賢」,而不是有血緣為之基且已經被承認與接受的「祖先與子孫能相感」的文化論述。
朱子的疑問與追問,是「祖先因有血緣之根,故能相感。」「相感」即「古人與今人」能「共在」,「祖先」能在「子孫」於家廟之祭祀中,如親臨而享牲,因之在感應中,感受到了祖先之在此,並且與我共在此一「祭」的世界中,故曰:「相感」即「共在」,代表著祖先的親臨,「死者」與「活者」的「面對而共在」,「逝者」與「在者」的「相感而共在」,「曾在者」因「正在者」的遙向---子孫的祭祀---而於「現在」的「相感」而能「見在」、「共在」。對朱子而言,能如此的根源在於「血緣之根」,「血緣」是其根,這便是「人倫」之意義,「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婦」,「一陰一陽」、夫婦、子孫、宗法與宗廟,正是子孫祭祀祖先意義的源頭。
然而,對朱子而言,不具「血緣」的「先賢」,能否成立在鄉祠、書院、精舍、孔廟中成立其「仿祖先」之可祭、可拜?正是一個追求形上之基的大問題。如果不能尋求到一個可支撐起整個「無血緣性」的「孔廟」、「鄉祠」中祭祀先聖先賢的形上之根源,則儒學之有「廟」亦終只能是如民間信仰中之拜神、拜英雄之「信仰觀」、「鬼神觀」而已,而不是一個歷代儒者從人倫與教化上視為大根與大本的「道統」,也不能在實存性上作為仰視聖人、聖人昭昭臨在的「聖賢觀」!朱子之問題正是在此。孔廟中祭統的根源課題,就是朱子的問題,也是今日我人應當面對與體悟者,此一問題何以是一形上根源的課題:「孔廟」、「鄉祠」中能祭祀「先聖先賢」的根、源何在?
二、 朱子對祭祀先聖賢的思索與黃榦的回應
(一)「文本中的在」與「不在之在」
朱子與象山、陽明之不同,特在於其相信「聖人之訓」可以經由作為書寫的文本在歷史之流中流傳下來。因而「古聖先賢」其人的生命在世雖已不在---由於人皆有死亡的極限;然而,「書寫文本」卻可以越過此一極限之邊界,在聖賢「死亡之後」仍然在歷史與後世中流傳下來,後世的人「閱讀」這些「聖賢典籍」時,仍然可以經由「文字與章句」、甚或是注解,而與「文本」中的「文義」生發感知與感應,此之謂「精神」上的「相通」。因此,雖然人皆有死而精神可以不死,緣於聖賢的「遺訓文本」所具之能夠比死更久的「在」,閱讀「遺訓文本」便是閱讀聖賢之「在」。古聖先賢雖已「不在」而猶可曰「在」。因此,朱子必然要為「四子書」重新作出「章句」與「集注」的「文義」解說,因為「文義」就是「聖賢之在是」;也要為「四子書」重新作出傳承的歷史與時間系列之系譜,此即「孔—曾—思—孟」。
然而,我們進入孔廟之時,存在於廟內世界的,並不是「文本」,而是模擬的「如在」之「神主牌位」或是「神主像(圖像或塑像)」,一但我們立於其前,相對之際,不僅有著在縱向時間上已成歷史---聖賢已逝---之如何「能在」的形上學與存在論之課題,也有著「沒有血緣」的如何「能祭」的如何「能相感」的形上學與存在論的課題。
(二)「孔廟中的在」與「不在之在」
有關於對祖先作為一已逝者,亦即是「不在者」,「祭」是令「不在」者「在」的禮儀,其意義則《禮記》<祭統>篇有云: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8]
顯然祭祀祖先的「宗廟之禮」在儒家者流的發揮之下,已經成了內在論述其意義的「兩代之間」的一種上下關係,而由下對上--也可以說即是「少對老」、「子對父」、「子孫對祖先」的關係上而強調了「孝」。一種在世關係的「孝」與生者對死者的「孝╱祭」。《禮記》<祭義>篇: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9]
《禮記》<中庸>篇:
宗廟之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者也。[10]
顯然,「祭先賢」乃是由「祭祖先」轉來,因為「祭賢」與「祭祖」皆是「祭先」,於是「事死如事生」的態度也就成為兩者共同的基調。問題是,「祭祖」乃以血緣作為「相感」之基,沒有血緣,僅有師弟相傳承與文化的傳承自任者,即便是「仁以為己任」,又如何能有「相感」呢?
朱子對周濂溪於鄉祠中立像而行祭祀之禮,實不只一次,抑且以程顥、程頤等北宋諸儒從祀與配享,可見朱子此時已然確立周濂溪為「孔孟」千載之後的道統之傳。朱子在鄉祠中祭祀周濂溪時,多作有記文,如<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卲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等。<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記云: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先生熙寧中嘗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嵗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11]
是韶州為周子曾為官處,其後之知州事周舜元先有「祠堂」之建,主祀周子,並以二程配享,其後遂漸頹,十三年後至於廖明德重又建之,遂恢復鄉祠以祭周子之禮。在朱子記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其「香火之奉」「遂惰弗供」的用詞,正是「宗廟」與「家廟」祭祀用詞的轉喻之語。另外,在這裡我們也必須注意,朱熹顯然不是第一個為北宋諸儒建祠的人,至少在這篇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不僅韶州早有主祭州濂溪的祠堂,附於州學之中,而且以河南二程兄弟以之配享與從祀,也早就出現。<卲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則記云:
卲陽太守東陽潘侯焘以書來曰:
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焘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先生,而道以大明。……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嵗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12]
又朱熹曾於廬山朝拜周濂溪之書堂時,曾有詩云:
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旁。
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13]
陳榮捷先生曾將朱子自幼及長的這一類行動,包括對周濂溪的奉祭,以及為母擇地而安葬等統稱之為「朱子的宗教實踐」。[14]田浩氏則認為朱子的祭祀先賢是與其「道統觀」有關。[15]
朱子對於「鬼神」的態度有著「兩重世界」的傾向,因而不僅他自己有著陳榮捷先生所謂的「宗教實踐」,他對於民間關於鬼神信仰的態度也傾向於「信其有」與寬容。因而使得他與湖湘學友張南軒有著明顯的分歧,這在他與張氏的通信中十分明顯。田浩的論文<朱子的鬼神觀與道統觀>對此作了清楚的分析。[16]例如朱子對於民間所信有關「死於非命」之「厲鬼」,便以理氣論來論證其可能與可信的存在依據:
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17]
田浩氏根據Ellen G. Neskar的研究,指出朱子和張南軒都想通過「為鄉賢及先賢立祠」來擴大與深化「祭師」的傳統,並且也企圖為建立先賢祠提供合理的基礎。[18]他們首要的建祠之先賢對象,當然就是北宋的周濂溪與程氏兄弟,這與其道統觀念有關,也與朝廷在孔廟中合法的以國家典禮來祭祀王安石的背景有關。儘管朱子與張南軒在若干「鬼神」與「祭祀」的禮儀與禮義上有其分歧,如張南軒反對朱子所贊成的「召祖先之靈」之「召靈」之祭禮,但朱子能以「祝文」與「告文」來「奠以告 ,尚其昭格, 降庭止,惠我光明」,來請求祖先之靈,並擴大到孔子以及其他的先賢之靈,能夠在「祭祀」中以「神」的姿態而降臨,而「臨在」於「祭者」並且與之相感。如<奉安濂溪先生祠文>記曰: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继孔、顏,下啟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闻其聲,如睹其容。……熹欽誦遺編,獲啟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宮,並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19]
在這篇奉安告文中,不僅出現了周濂溪的「先生之靈」與「臨鑒之」,並且周濂溪還是一個有意義的「中介」,正是周氏能夠上继與下啟,傳承先聖於千載之後,是故朱子也定然可以通過周子的「臨在」,而「接上」先聖先賢的「臨在」。「如睹」與「如聞」正是通過周子而得到的「聖賢之容」與「聖賢之聲」,是故朱子通過周子,也能在「祭如在」的世界與「先聖之靈」得到「感通」。<屏弟子員告先聖文>中云:
熹不肖,……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為淫慝之行,……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耻以明刑。……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20]
用的也是「臨之在上」的一種「臨在」式的用詞。因此,朱子不僅是要通過先聖先賢的立祠來確立道統而已,根本上除了「文本」與「文化」上的「道統」之外,他還企圖於「孔廟世界」中成立他的「祭祀與道統」之關係,更進而,他希望周孔時代以血緣為之基的「聖王設教」,能夠在今日是以孔孟為主的「聖人設教」,通過祭祀與教化而普行於民。以血緣為之基只能是宗族與家庭的「祖先」與「宗廟」,而朱子卻是想以「道德教化」為其主軸,確立「作之師」的一種以「師--弟」為文化傳承的主軸,其根源則在「孔子」;孔子之後,則係一以「先賢往聖」所傳之「道」為主的「傳道系譜」、「宗傳系譜」---一種在復古文化意含上乃是「仿」於「宗廟世界」的「道統世界」;並且在與之「聯繫」的「祭如在」之關係上,確立出「祭祀先賢往聖先師」的「教化性」及其可普及性,一如上古的君主以「血緣」、「人倫」、「祭統」為「設教」精義的核心,朱子也欲以「聖人—以孔子為源」的「道」來作為「設教」精義的核心。除了國家級的「孔廟」之外,更欲在地方州學郡學皆能有「鄉祠」之設,以祀「先賢」,則不僅「先賢往聖」能仍存於今日之「祭」與「所祭」之中,「聖賢之道」也能傳下而行於今,使以「聖賢」為主的「教化」能因「祭祀」與「鄉祠」的普及而普及於天下。一些西方學者將朱子在許多地方州郡學為周子建祠的動機,解釋為建立道統並且對抗朝廷孔廟中的王安石之從祀,確實是一種頗具洞察的卓見,但若將之完全歸為朱子與張南軒的首創,而且將朱子關注祭祀先賢與先聖的動機僅止於「外緣性」的考察,而忽略他對儒學理想與教化在實踐方面的特殊性,則顯然是不符實情的看法。
朱子具有「二重世界」的傾向性是今人徐復觀先生提出的觀點,用以指出在朱子一生的行為中所出現的許多卜筮、覓墓、以及在《易本義》上許多與程頤《易程傳》相異之處,都不偶然(事實上,《朱文公文集》的卷八十六中,充滿著「祈雨文」、「謝雨文」、「祈晴文」、「謝晴文」、<請雨謁北山神文>等此類文章),徐先生於是為文<程朱異同-平舖地人文世界與貫通地人文世界>[21],指出朱子實為一「二重世界」者,並與二程之「一重世界」作出了極富意趣的比較。徐先生的這篇論文,使我們注意到在朱子的一生中,其實際行事並非只有純粹的依「理」而已,還有「氣」的世界,而徐先生也藉此來判分出「程朱異同」。徐氏的觀點正好與西方漢學界中關於朱子的宗教、信仰、祭祀實踐等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這樣的研究呈現了朱子的另一個面向,也使得朱子在南宋伊洛之學南傳復興,意圖為程氏之學爭正統之外,朱子的獨尊與獨表周濂溪,並為其廣立鄉祠之事件,除了哲學意義(如「無極而太極」的<太極圖>與<太極圖說>之推尊)與文本意義(如《近思錄》的卷首)之外,也有著惟有朱子才會賦予關注與聯想的「祭祀」意義。由「伊洛之學」或「濂洛之學」的「道統」關注到「統」的祭祀性問題:祭祀孔孟、祭祀先賢往聖、祭祀「無血緣性」的先人。換言之,朱子由祭祀周濂溪於鄉祠之中所開出與面對的問題與課題,亦即就是「孔廟世界」所以能成立的形而上的問題與存在論的課題。「祭祀世界」與「孔廟世界」如何能夠有其存在之根源與其基礎,尤其自「宗廟世界」與「祖先—子孫」而來的「孔廟世界」與「師—弟」、「先賢往聖—後學後人」如何能有存在的根源與基礎而能行其「祭祀」,並且在祭典禮儀中有其神聖性而使「聖賢」受到後人景仰,成為歷史文化的核心?朱子顯然在南宋的洛學系統中,藉著「鄉祠」而「祭祀」、藉著「鄉祠」普行「教化」的思考,使朱子成為一個特殊的思考者與行動者。
朱子在祭祀祖先與先賢時,既「召其靈」,如前所述引,冀以望其祖先或先人之「靈」能降而「臨在」,則顯然朱子祭祀的形態已是一「祭其神」的狀態,而此「神」又是一「死者」在其「死亡之後」的「死後」狀態,因此朱子的「召靈」實有類於《禮記》等古籍中所記之祭其「神」而祈其「臨在」的形態,不論是朱子的「召靈祭神」、還是「祭鬼」,「神」與「鬼」都是一種「祭」其「死後」狀態的類型,而非「祭」其「生前」狀態的類型。這一點正是徐復觀先生之論文 <程朱異同>的意義之所在,它提醒了我們去關注朱子的「兩重世界」之傾向及其「鬼神觀」與祭祀祖先、祭祀先聖先賢之理的關係,以及朱子的「祭神」特色係源自於其有著「召靈」以求「先人先賢」能「臨在」,乃是一種「祭」其「死後」狀態的類型。這與朱子的編輯與注解《四書》,企圖通過「在歷史中」的「文本」來呈現的「先聖」與「先賢」之「生前」的進路,顯然是不同調性的,分屬於兩種不同類型的「存在論」。一為「死後」、一為「生前」,一為「祭神」、一為「祭人」;一者是求其「神」能「臨在」而與作為後人與子孫的我之「相感」、一者則是求其能通過「歷史之中」而得以使「已死者 / 過往者:祖先、先聖、先賢」能在「文本」中呈現出其「生前」,「文本」在「歷史之中」的流傳及其與後世「閱讀者」的「相遇」即是兩者之「相感」。而後者顯然是朱子與二程同屬的「一重世界」之屬性,前者卻是「兩重世界」!二程---尤其是程頤---的「一重世界」之屬性,徐復觀先生稱之為:平舖的人文世界。我認為即是指一種「理世界」的理想性,這種理想性尤其存在於古往今來的一種「往聖今在」的歷史世界中綿延、傳遞,中間的關鍵便是「能學」的「士」與「能教」的「師」;因此,就「古今」的「歷史世界」而言,它是「一重性」的,就「當下」的「世界」而言,它亦復是「一重性」的;此與朱子以「祭神」、「祭祖先」的「臨在」,具有天地、上下的「降臨」之「兩重世界」義,顯然是不同的。
朱子既然以「祭神」之方式來「祭先人、先賢」之「死後」,冀其「神靈」能降而臨在,則在朱子那裡,我人(祭者)所以能與此「已死者/神靈」相感與感通之「理」,何在?朱子的思索與回應,仍然是「理氣論」式的。朱子認為,祖先之靈能夠「臨在」之「理」,關鍵便在於兩者之「氣」的能「感格」與能「感通」。對「往者╱死者」而言,其雖死,「氣」卻未散盡,仍在此天地之中;對「活者╱今人」而言,無論是死者之後代子孫,還是不具血緣性的後人,就「血緣性」而來的「祖先—子孫」、與「非血緣性」的以「道」為其「文化聯繫」而來的「先人(聖賢、師)—後學(仰慕者、私淑者、弟子)」,都可以從「氣」上而立論其「能相感」之根與源,因為朱子的「氣」,乃是一「天地萬物一體」的「氣」,故具「能相感」之「理」。《朱子語類》中記云:
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22]
只是這個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23]
又曰: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24]
朱門弟子所問,我們可以遙想並且會心,因其所問,正是我人在今日亦想提問者,蓋問者所問,正是在問「能感格」與「祭如在」的所以然與存在之理為何也!朱子的答覆,顯然是以理氣論來思考「所以能祭祀」之「理」與「實」。「畢竟只是一氣」,不僅是指祖先與子孫,亦可言先賢與後人,此所以子孫與後人能祭祀之理,在於其「氣」能相「感格」與「感通」。朱子言「感通」之「理」,在於「氣」之聚散。故「已死者」仍復可以聚其已散之「氣」,其關鍵在於「生者」是否能在「祭」時與「死者」藉由「感格」而「相通」。故「能感通」實為「祭如在」的根源之所。就「祖先-子孫」而言,「能感通」之本在於其「血緣性」,「畢竟只是一氣」,故曰「血氣」,亦曰「血統」。然而,「非血緣性」的「氣」能否有可以「感通」之「理」呢?朱子的答覆是,其「氣」仍復可以「感通」,以其「氣」仍復可以來「聚」也!《朱子語類》中記云:
陳後之問:「祖先是天地間一個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地,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個相關處。」[25]
又曰: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只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26]
在朱子與弟子的問答當中,朱子話語一轉,又提出了一個「公共之氣」,並且將「血緣之氣」亦統歸於此「公共之氣」。顯然正是企圖要為「子孫-祖先」的「家廟」與「宗廟」之外的「聖賢之祭」能否得以成立「感通」,尋求一個「理氣論」的存在根源。「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故其「祭如在」以及其精神魂魄之「氣」可以長存之久,顯然是超過了「人倫血緣」的「五世」。問者所問,正是問到了核心:聖賢乃是上古「民不祀非族」的「非血緣性」者,則其可以「常在」之「理」何在?朱子的回應反映出他的思考仍然是企圖由「氣」來尋求「能祭」並且「能祭如在」的存在之根源。因此,對於聖賢之祭祀的「祭如在」之成立,關鍵仍復是在於「氣」的「感通」。在《朱子語類》中,朱子舉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特例,由此一特例,更是可以看出朱子欲為「非血緣性」的「祭如在」尋求存在論根基的用心。《朱子語類》中記朱子之言云:
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個亦自浩然日生無窮。……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27]
朱子自「子孫」之外言之,以「無子孫」者為例,說明其「氣」亦未嘗散盡,「難不成無子孫他氣便絕無了」,朱子成立「血氣」一詞,正是為了「非血氣」之「統」的祭祀,可以在「道統」下成立祭祀先聖先賢之可能。
由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朱子所給予「子孫祭祀祖先」與「後人祭祀先賢」之「理」,在於人雖已死而其「氣」仍然散在天地之間,故可以無古今之間格,而可以有「相感格」之「理」,此是朱子所面對「祭如在」之形上問題時所提供的理氣論式思索。此種思索,顯然與張載的「太虛為一氣」相類。但實不如謂與二程之「萬物與我為一體」言說為佳。二程說孔之之「仁」,以孟子「萬物與我一體」為說,謂:體「萬物與我一體」處即是「仁」之發端。此義亦正貫「孔孟」為一,此便是朱子所謂「一氣感通」之通死生、幽冥、往來之「理」之所以。萬物既與我為一體,則先祖、先賢亦皆是與我為一體,不以此身為杆格,不以此生為間斷,血緣可以生生,歷史文化可以綿延,「血緣在」則成為「人倫在」之根源,「聖賢在」則此一以人倫教化為主之歷史與文化亦可以常在而長存於後人與後學之相感中,成為「聖賢」可以成為「往聖、先賢」在「歷史文化世界」中能有「現在」,對「將來者」而言亦有「往者、先人」。所以不僅是「祖先-子孫」能相感通於「祭」中「如在」,「非血氣」的「非血緣性」之「先聖先賢」亦因其「氣」能有相感通之「理」,聖賢之祭祀也就有了意義,「道」的傳承即便是在「無子孫」者處也能因其能相感而繼續流傳,並且甚或對於「有子孫」之大儒或先賢而言,他的傳道與相感便不一定是以「血氣」與「血統」的子孫為流傳之基,而更有可能是以「師」的身分而以「弟子」為其「道統」的授受之基。是故朱子之以理氣論提出「祭如在」之存在論思考,實則道通於二程之以「萬物與我一體」來道通於孔孟之思考。能「體」此處之發端即是「仁」之發端,「仁心」即是「祭心」即是「孝心」。「仁」之「萬物與我一體」是一個存在的根源:此即朱子所稱的「公共之氣」。子孫以血緣而行祖先之「祭」,《禮記》上稱之為「孝的綿延」;非血緣之後人後學行其對「先賢往聖」之「祭」,則是「教的綿延」。在此兩種綿延下,歷史世界與文化世界乃以「先祖宗」與「先聖賢」而「在」於後世的「子孫」與「後學」之世界中。
朱子對於「祭先聖賢」的「如在」之思考是否已然完全地回應了「孔廟世界」的形而上學之提問,他的理氣論是否已然對「祭如在」的可能給予了完善的存在論的解釋,尚有待於我們能否對於朱子之說做出近代性的再評價與再理解。然而,至少從徐復觀<論程朱異同>的文章及陳榮捷在<朱子的宗教實踐>論文中所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出一種流行在西方漢學界的論點,即朱子本人實際上有著一種「兩重世界」的傾向,一如徐復觀的文章所指出的。徐氏的文章所給出的此一術語:「兩重世界」,對我們研究朱子的「祭聖賢」與「祭如在」極為有用。另外,在陳榮捷論文中所蒐羅列出的許多資料,特別是編在《朱文公文集》卷86中的許多「祈文」,可以證明朱子在「兩重世界」中思想的複雜性。無論陳榮捷的論文是否有其「在西方漢學世界中」的特定言說對像之限定,他在論文標題上稱之為「朱子的宗教實踐」,「宗教」與「宗教實踐」已經涉及到了「孔廟世界」與「祭的世界」的近代性思考。雖然陳氏的研究並未能就「儒學/道學」與「宗教實踐」的辭彙作出其中國與西方語境比較的判斷與分析。
朱子以「理氣論」之論說來尋求「祭如在」的形上依據,顯然地,並未能真正達到「存在論」的層次,抑且有著「鬼神論」的「兩重世界」之「信仰」之嫌,[28]不僅是在其「祭神」與「祭人」之有別,而且也在祭其「死後」與祭其「生前」之有別---後者方能謂是朱子編注「四書」以求「聖賢遺訓」之「道」之意義。因此,張南軒的不贊成朱子之「召靈」,不是沒有道理的。對於朱子的「祭其死後」與「祭神」之「祭如在」意涵在「祭的世界」與「孔廟世界」中的探索,其弟子黃榦繼續了這個課題。
(三)黃榦對「祭如在」的思索與回應
近代學者中,對黃榦之祭祀論賦予關注的,首推錢穆先生。他在<中國思想史中的鬼神觀>一文中,有一小節專論黃榦的祭祀論。[29]錢穆先生所據以論者,主要在黃榦下列的一段言說,可以看出,黃榦的言說其實正源自於朱門求學時代,如《朱子語類》中所記朱門師弟對「祭祀與鬼神」之討論。黃榦在〈復李貫之兵部〉中申己說云: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為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為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為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為說,以為只是祭已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為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所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30]
自黃榦的〈復李貫之兵部〉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朱門高弟間對於此一問題的討論及其紛歧,黃榦所針對的討論參與者,尚包括了他的同門李道傳、葉味道與胡伯量等人;而黃榦在此書中的連續兩個提問,都非常根本而扼要:一是問只有「聚己之精神」,如何可能「祖考來格」?可見黃榦完全不認為「祭如在」僅是一種相對主義式的「祭者」之「模仿」義活動;他並且認為如果「果爾如此」,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古昔聖人與經典又何必常謹言之,故其問曰「何耶」?黃榦從至親之生、歿的孝慕與交感來言說「祭如在」,應當是子孫與父祖先人間的「神氣交感」,是「祭者╱生者」與「被祭者╱死者」的「共在」世界之實有。黃榦的第二個問題,則是已死者「氣」已散,雖曰其「氣」仍為「公共之氣」而尚存天地之間,但如何可能在「祭」時能使其已散之「氣」復「湊合得其為之祖考」?黃榦認為關鍵在於「生者之精神」與「祖考之氣」之間的「神氣交感」,若能,則「祭如在」之「如」便是「洋洋然在其左右」矣!對於第二個問題,黃榦的論說顯然是存在論式的,他並且以「琴、聲、指」為喻,其云:
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鏘然矣。謂聲為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即然而無聲,謂聲為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為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著心胸,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31]
黃榦「琴聲-絲桐-琴指」的「南風之奏」比喻,其所欲傳達者,正是面對了其師朱子「祭如在」諸言說中的困境,而以此「琴聲之喻論」來繼承與發揮「古」與「今」、「死」與「生」所以能夠「感格之理」。「古聖」並非「不在」、「死者」也非「不在」,通過「生者」、「後學」的「琴指」,與「今人╱生者」的「絲桐」之相會,則「琴聲」自然「奏」於天地之間。「古人╱往者」便是「祖考來格」,豈有單憑「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可以使「南風之奏」再現其「琴聲」者?「琴曲」之音聲能繚繞於世界之中,乃是因為緣於「絲桐」與「琴指」的「相會而撫」,而「祭如在」所以是一個「共在世界」,也是因為根基於「無所受於祖考之精神」與「祖考存於天地之氣」能夠「神氣交感」,是「生者」與「死者」、「祭者」與「受祭者」、「子孫」與「祖先」、「學者」與「聖賢」的「交感」而使「祭」的世界當下成為一「共在」的世界。黃榦的「琴聲喻論」顯然不只是針對「祖先」與「子孫」,在「血緣性」之外,對「非血緣性」的「先賢往聖」與「弟子後學」顯然也能適用。因此,當「道」便是古人的「絲桐」時,後學者以慕道與向道之心來「以指撥弦」,不僅是「聖賢文本」,即便是「孔廟世界」中對於「聖像」、「木主」的「面對」,也能產生「琴聲」的「共鳴」。由是,「前人」與「後人」的聯繫關係便可以稱之為「統」,「統」便是「琴聲」。「血統」是「子孫之祭」與「祖考來格」的「神氣交感」,「道統」則是「後學慕道」與「聖賢先師」的「神氣交感」;「交感」而「共在」,「指撫絲桐」而「共鳴」。至於是否為「南風之奏」或是「優入聖域」,則是境界問題。如此,依黃榦的理論,不僅是「祭祖」時「祖先」是「在」的,於「子孫之祭」時「交感」而「共在」;同時,在「祭先聖賢」時「先聖賢」也是「在」的,在「弟子」與「後學」或「私淑」之「誠敬面對」中能「交感」而「共在」;同時,朱子所一生致力的「聖賢文本」中的「聖賢之遺訓」也是「在」的,在「弟子」、「後學」之「閱讀」與「理解實踐」中能「交感╱感通」於「聖賢之意」而「共在」;因而「學道」與「傳道」便有了「師—弟」這一層具有根本性意義的關係之能成立。在黃榦的論說中,「道統」之「道」因而能在存在論式的基礎與根源意義上,有效地取代「血緣」成為「古╱今」、「先聖╱後學」、「師╱弟」在「道的世界」之中能「感格」與「感通」之基因。將「道」取代「血緣」,使「道統」取代「血統」成為歷史文化傳與承的根本,「聖人之道」的「傳與承」,不在乎「血緣性」的「血氣」與「血統」,而在乎「非血緣性」、「公共之氣」的「師」與「弟」之「道統」。「孔廟世界」中「受祭」的「聖賢」與「先儒」牌位,皆非同姓,便已經說明了此點。
三、「祭如在」的兩種進路及其世界
-「如」的「模仿世界」與「如」的「共在世界」
(一)「如」的模仿義
我們將從「如」字切入以致思於「祭如在」之意義。並將「如」字的本義:「模仿」及由此所構成的「祭如在」之模式稱之為「相對論」的思考模式。在此模式下,「如」所構成的「祭如在」乃是一「死與生的相對」、「往者與現在的相對」、「先聖與今學習者的相對」,由是,「如」的「模仿」義乃為了構成一個「彷彿」死者「仍在」其生前之時般,使生者可以進行其「祭祀」或「行孝」行為於此一「模仿」之對象。此即《禮記》〈祭義〉篇所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與《禮記》〈中庸〉篇:「宗廟之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者也。」之義。「事死如事生」與「事亡如事存」,「死」與「生」的關係正是「生者」之對待「死者」為一種「如」其「生」,「亡」與「存」的關係亦是「如」的關係。這乃是一種以「生者」為主的對待「死者」的「如」之態度;「如」的意義乃是一種以「模仿」--模仿「生前」、模仿「未亡」時的致祭與至孝之行為模式的儀典與意義之建構。因此,「模仿」乃是構成兩者關係的本質。在此一理解下,「如」字是一種以「模仿」來聯繫A與B兩者之間的模式。我們稱此一「如」所構成的「祭如在」之世界,為一種相對論模式的「如在之世界」。
此處下一「模仿」義的「如」字,便意味著「祭如在」之活動與行為意義的本質,乃在此而不在彼,謂在生而不在死,亦意謂著在「在者」而不在「不在者」也;謂在「人╱生者」而不在「鬼神╱往逝者」也。「在此」、「在在」、「在人」,則「如」的相對論模式成矣!祖先與先人因為「在此者」的致祭與行孝而能「彷彿」是其「仍在」「宛在」,於是乎「生—死世界」乃因著「敬」「思」「孝」而得構成為一有血緣或無血緣的「兩代世界」,聖人設教之精義便係以「血親」而致孝、致祭來聯繫死生為其大事,使兩代之關係成為一綿延之建構,「血親」是「人倫」之綿延,「非血親」是族群中「聖賢」之綿延,兩者共同構成了「文化綿延」。天地之道肇端於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生命的本質在於傳遞與綿延,此之謂生生之道,兩代之間的關係建構以「祭如在」來作為聯繫兩代—生死、古今的意義,正是以「血緣」作為聯繫核心的表現。無論是「相對論」的「模仿」還是「存在論」的「共在」,其目的與意義都在於指向一種對於兩代之間關係模式的必須聯繫與建構。由「祭如在」來建構與致思其聯繫方式,正是因為從「血緣」關係作為內在性出發的源頭,形成了「祖先」與「子孫」的「宗廟」傳統,因此,無血緣的「孔廟」之致祭的「祭如在」之思考,也必須站在這個立足基點上來致思,才能得其歷史之實。
《禮記》<祭統>篇中所描繪的「齋」之意義:
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其者。[32]
正是一種「模仿」義下的「祭如在」之今人、活人、親人生者所作的對於上一代---死者、往者、親人之「孝」的表現之於「祭」時,那麼,當其誠心與誠意之時,被其所「祭」的「不在者」,相對於「在者」而言,究竟「不在者」是否能是一「不在之在」呢?在「孔廟」之中,當「致祭者」或「致敬者」對「不在」的「先聖」與「先賢」行其「致祭」與「致敬」時,究竟「不在者」是否「在」呢?「不在者」如何可能與可以--對「在者」而言--「在」呢?
「祭如在」的「如」字是一「模仿」的意義建構,與相對論模式的只能有「我在此」的「生者」之單一活動與單一建構,這乃是最通常與通行的認知。無論是鬼神世界、有血緣的祖先世界,或是無血緣的聖賢世界,對「如」字的「模仿」義的解讀,也就成了聖王或為君者為了治理百姓的「神道設教」,而尚不能成立為一種對我而言就是具有意義的實感。如同黃榦的「琴聲喻論」所欲傳達的「交感共在」的「琴聲共鳴」之世界。是一個「祖先與我共在」或是「先聖先賢與我共在」的世界,一如黃榦所言的,並非只是因為我想我欲我思,故只是單單「聚己之精神」,來一場「模擬」之遊戲,朱子自己也曾說過:「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可見朱子對整個「祭如在」中「祭」的思索與認知是傾向於一種「共在」可能之追求的;必須是真有其「神氣交感」的「共在」之可能,才會激起我們現在的子孫對於先人「致祭」的真誠行動--「孝」的本質在於先人與我、我與子孫皆有可以感通之理與可以感通之氣。同樣地,現在的後學者對於可以尊、可以敬的先聖先賢「致祭」也必須是真有其「神氣交感」的「共在」之可能,才會真能引致「致祭」與「致敬」之真誠行動--「敬」的本質在於人人皆可以向上而為聖為賢為人,以是在此點上有其可以感通之理與感通之氣。於是,對於「如」字字義的探尋與解讀,我們終究還是要嘗試走上存在論式的思考,致思於「共在世界」的可能。
(二)「如」的共在義
其次,另一種致思於「如」字的進路乃是探詢有無可能以存在論來達到一種「祭如在」之「共在世界」的可能,「如」字能否傳達出一種存在論的訊息:「生與死」、「往與來」、「先聖與後學」可能「共在」的「共在世界」之訊息及尋解其根源的致思。
《禮記》<祭義>篇中載有孔子與宰我論鬼神之事: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33]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因此,如果祭其「死後」,則是「祭鬼」。《白虎通》釋「宗」曰:
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34]
《釋名》則釋「廟」曰:
廟,貌也,先祖形貌之所在也。[35]
由漢代《白虎通》與《釋名》所釋,則顯然周人的「宗廟世界」乃是一種「祖先」之「生前」的「可知的」世界,而非「死後」的、「不可知」的「鬼神世界」。「先祖形貌之所在」已指向《釋名》所認知的「宗廟」一詞之原始性,乃是一「祖先」之以「生前」狀態為「後人」所「尊」之的「世界」,這個世界存在於活著的子孫為其所構築出的殿堂之中,殿堂稱之為「宗廟」,有其「可尊」的神聖性,有其天子、諸侯、卿大夫已迄於士的典制。
另外,我們在先秦許多文獻典籍的記載中,如在《禮記》中看到的祭祀儀典中出現的「尸」的記載,多係以活人--「死者之孫」來扮演「死者」,目的也是為了彷彿「死者」之「生前」。《禮記》<郊特牲>云:
尸,神像也。[36]
<坊記>篇則云: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37]
<祭統>篇云: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38]
清人莊述祖所輯《白虎通闕文》<宗廟>一則有云:
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親之無形,升之阼階,仰之 桷,俯視幾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39]
唐人杜佑《通典》即以為此乃「孝子之心」,故有以「尸」仿活人以遂其「祭」意,其云:
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40]
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41]
故祭祀所以有「尸」者,乃是一種「如在」的意圖,係在「木主」、「神像」之外,以活人仿之,在祭祖先時,則以死者之孫仿之;[42]故「尸」實與「木主」、「神位」、「神像」之意義相同,都是一種自死者之「生前」來表達在孝子與後人的世界之中,死者仍然「如其在」。「尸」的作用就是「如」、就是「像」、就是「象徵死者」之「仍在」、「如在」。「尸」以活人來扮演與象徵,這種意義的指涉尤其明顯,係指向於「死者」之「生前」的狀態類型之孝思。這或者可以解釋「孔廟世界」中先聖、先賢: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先儒的「象徵」,雖然是以「木主」為主,然而,也有「畫像」,甚至塑像之故。故朱子亦以為當時所聞蠻夷傜族之風俗中,以「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在行祭祀之時,「話語醉飽」,此「用尸之遺意」,朱子以為正是「古之遺意」。[43]顧炎武《日知錄》中則討論了「尸」與「像」的演變,其云: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實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44]
要之,無論麻嬰為尸、以弟為尸,或是「尸禮」與「像事」,皆是一種對祖先、對先賢行其「如在」、以「尸」以「像」而「象其生前」的祭祀行為。是一種以「如」其「生前」的狀態來行其「祭祀」的「祭如在」。如是,我們可以確定,「祭」有兩種狀態:一種是以死者之「死後」的狀態來行其祭祀,此即是「鬼神」之「祭」。既然人必有死,曰鬼曰神,皆是在進行對「死者」之「死亡」之後的狀態之認知,此認知與「人死」有關者,即為「鬼」與「神」。對「鬼」與「神」的祭祀,便是一種屬性於「死後」狀態的「祭」,這乃是一種「宗教性」的信仰。另一種則是不祭其「死後」而祭其「生前」之祭。其實不論是「死後」還是「生前」的用詞,皆是指向於「死者」之已然「死亡」之後,然用詞不同,則其指向的狀態與意義上的意向性也不同。在「死者」「死亡」之後,去祭祀其「生前」的狀態,行其紀念之心、紀念之思、紀念之意,這正是《禮記》上所云的「孝之至」也之意。在《禮記》中諸篇所論的「孝」與「祭」之義,大都朝向此一種「祭」其「生前」的意義來發揮,主意在其「生前」,故此一種「祭」其「生前」狀態之「祭義」,乃是「祭人」,相對於「宗教性」,此乃是一種「歷史性」的「不朽」意義下的「祭」。既非「祭鬼」,也非「祭神」。
要之,「生前」與「死後」都是「死者」之「死亡之後」的狀態,「祭」的本身,已召喚著一種對死者已死的情緒與情境世界,「生者」---無論是「子孫」還是「後人」--對待「死者」的方式,便是「面對」,「面對死者」:是「面對其生前」?還是「面對其死後」?顯然地,我們在本文中所主論的「孔廟世界」,在其中的「面對」,應當是一種「生前」形態的「面對」,無論在今日東亞諸國現存的「孔廟」與「文廟」,廟中供放的不論是先聖與先賢的「木主牌位」還是「畫像」或是「塑像」,都可以意味出「孔廟世界」與「宗廟世界」的同質性,乃是一種「祭」、一種「面對」其人「生前」的「召喚」,無論是孝子、子弟還是後學、弟子。因此,當「生者」在「面對」時,一種「敬」的態度便被強調,《禮記》中言「敬」,它書文獻記載亦然,《國語》<楚語>中云:
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之,如或臨之。[45]
《禮記》〈祭統〉云:
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
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46]
<祭統>又云: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於心也。心恘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47]
「祭者」若不能「自中而出於心」,則何能達於是「祭」?「祭」的狀態既不能成立於「敬」與「誠」,便是連「彷彿」的狀態之「如在」亦談不上,更遑論「交感」的「如在」的「祭的世界」之「在」!「宗廟世界」的「祭者」如此,用「齋」以為其「敬」的「致祭」儀典程序;則更何況是以「聖賢」的「可敬性」為主的「敬」,在「敬的世界」中成立「古今世界」的歷史性、文化性、綿延性。當「聖賢」以「木主」或是「像」存於「孔廟世界」中時,「祭者」或「致敬者」也仍然需要的心靈、精神、態度便是「敬」。沒有了「敬」,就不可能成立「如在」的世界,不論是「模仿」義的「如」還是「共在」義的「如」。<楚語>中的「如或臨之」便已然很好地傳達了「面對」的本質,無論與「所面對者」之間,兩者所形成的「如」,是「模仿」的「臨在」,還是「共在」的「臨在」;總之,「祭如在」的世界,是一個以「生前」狀態為其「祭」與「面對」為主的世界之構成。
後 記
此篇論文初稿曾在韓國漢城成均館大學「國際儒教文化圈會議」上宣讀,當時之評論人於評論文中還是向筆者提問了儒學究竟是否為宗教的問題?筆者的回覆,係以為提問的本身,隱藏的是其「前理解」中仍然深崁著「近代化」與「五四新文化式」的烙印,即以「宗教」來格義東亞儒學與中國儒學,終而提出儒學「是否」為宗教的議題?這個近代以來的學術文化課題已主導了學界研究的思維,包括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一、二代新儒家,及大陸的任繼愈、美國的陳榮捷、杜維明等,莫不如此。筆者的論文標題所以名為「議題」者,正是不欲在此一格義模式上打轉,筆者係重新看待此一歷史存在的課題,欲自一個根本處重新提問,以形成一個新的視域與角度的議題,自存在論提出反思與回應,以開啟一個可能的課題與論域。誠如正文中所言,筆者一開始便未從「宗教性」入手思考「宗教與儒學」,也未在儒學「『是否』為宗教」問題上定位論文研究的座標。筆者並請提問人注意筆者論文中的一組術語,即「死後」與「生前」,這一組語彙係筆者在論文中亦欲就「人死亡之後的存在」而區別出的兩種樣態:前者乃「祭神╱鬼」,後者則為「祭人」。儒學的文化與歷史,無論在東亞地域中的韓國或日本,皆是以後者為人文性之主軸而向聖賢文化與學習聖賢文化而發展。稱名上的「三教合一」、「儒學」、「儒教」,尤其是「教」字,是否便能以「Religion」來作格義與比較,已經不是筆者的課題與承擔。筆者認知的「教」很簡單,便是以「人文╱人倫」為主的「儒學」應當如何「教化」的「教」義。
作者 謹識
[1] 李紀祥〈理學世界中的「歷史」與「存在」〉,收在《道學與儒林》(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10月),頁263-346。
[2]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3月,全集校訂本初版二刷),第五篇〈死生之說與幽明之際〉,頁97-112。
[3] 錢穆《靈魂與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年6月,初版三刷)中的〈中國思想史中之鬼神觀〉、〈人生向何處去〉等篇,頁59-110;頁159-166。
[4] 參見保羅˙巴德和與琳達˙巴德漢合著,《不朽還是消亡》(高師寧、林義全譯,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必死的邏輯>、<復活、不朽及永生的意義>等章 節。
[5] 近代以來對孔子的儒學重新審視,並以西方的「宗教」作為參照而將儒學定位為「孔教」,企圖以為當時中國之「國教」,成立「中國孔教會」並發行「孔教會雜誌」者,是其中之犖犖其大者,如章炳麟、陳漢章、張爾田等皆是,其中更著名者,當屬康有為。陳漢章所主編的《孔教會雜誌》自民國二年(孔子紀年2464年)在上海創刊發行,這是在憂患危機意識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一種「西化式」的救亡行動。此外,杜維明、秦家懿、任继愈等皆有關於孔子的儒學是否為「儒教」以及具有「宗教性」討論的專門著作。杜維明的論說與思考,可以見其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此書已譯為中文:《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7),杜氏在西方的學術活動與多本論著,明顯具有與西方宗教與神學碰撞及對話的意含。 秦家懿與孔漢思所合著的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1989年由紐約Doubleday出版,德文版則更早於1988年由西德Piper出版,中文版《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吳華主譯,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7月)則於1989年7月出版;在德國學者孔漢思的〈序〉裏,所給予的標題是〈世界第三大宗教:中國宗教〉,標題呈現的認知其實便是以「Religion」所格義出來的「儒教」。任繼愈則曾主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一版一刷),惟所收論文均為1978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對任氏所提出的〈論儒教的形成〉的論文及環繞「儒教」此一問題的反響與討論、論辨之文章集。
筆者尤其想引述晚清同光年間的王韜在其《弢園文錄外編》卷一之開篇〈原道〉中的一段言論,來表明一種立場,在態度與研究進路上或許本文作者略有向此位晚清學者之銜接意。王韜云:
儒者本無所謂教,達而在上,窮而在下,需不能出此範圍。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從而強名之者也。我國以政統教,蓋皇古之帝王皆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貴有常尊,天下習而安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1),卷一,頁1。)
王韜所立之所,係站在「外王」之所來看此問題,與上述諸晚近學人之以「內聖」角度立言思維之位所者,有其異同。但王韜的〈原道〉轉向「外王」模式的視野與思考,正好對映也對反出韓愈那篇劃時代的〈原道〉之區分周、孔;則王韜在面對西法與自身危機感時,何以要繼承韓愈的這篇〈原道〉來作為篇名,則其所謂「道」者,頗值深看。筆者以為儒學之「教」,僅能稱之為「儒家」。儒者世界以「家」為本,「家」者:以血緣性為根源之「人倫體」。「儒家」中之不具血緣性之師生聯繫的文化與傳受,乃係以此為其傳述與習受之主軸。如此,則由儒家而來之儒教,其教與近世所謂宗教者之教,有異焉。
[6](吳)韋昭解,(清)汪遠孫考異,《國語》(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據士禮居黃氏重雕本校刊),<魯語>,卷4,頁6b。
[7] 此可參班固《漢書》中〈平帝紀〉、〈王莽傳〉所載。另、有關漢唐間廟學制的形成及其普遍化的歷史,參考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一刷),第一章「漢唐間學校教育發展的特質」。
[8]《禮記注疏》,(清)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1989年),頁830。
[9] 《禮記注疏》,(清)阮元刻本,頁806。
[10] 同上註,頁886、887。
[11] (宋)朱熹,曾抗美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卷79,收入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二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頁3678、3679。
[12] (宋)朱熹,曾抗美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卷80,頁3803。
[13](宋)朱熹,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卷7,收入《朱子全書》(第二十冊),頁492。
[14] 陳榮捷,《朱學論集》(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 ),頁181-204。
[15](美)田浩,〈朱熹的鬼神觀與道統觀〉,收錄於朱傑人主編,《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紀念朱熹誕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頁171-183。
[16] 田浩,同前註引文。
[17](宋)黎靖德編,鄭明等校,《朱子語類》(三),卷63,《朱子全書》(第十六冊),頁2091。
[18] 同註15田浩引文。
[1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卷86,頁4038。
[20] 同上註引書,卷86,頁4034。
[21]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頁569-611。
[22](宋)黎靖德編,鄭明等校,《朱子語類》(一),卷3,<鬼神>,頁158。
[23]同上註,頁69、170。
[2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卷3,<鬼神>,頁171。
[25]同上註引書,頁171。
[2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卷3,<鬼神>,頁170。
[27]同上註引書,<鬼神>,頁173。
[28] 這一點特別可以指出朱子與伊川間對於「鬼神」的差異,《二程粹言》中記有一條伊川對於「鬼神有無」的談話: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見楊時訂定、張栻編次,《二程粹言》〈天地篇〉,《二程全書》(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冊3,粹言二,頁2b。)
伊川的答覆真是好極了。現在我們能夠了解伊川如此回答的真正主因在於源自孔子的先秦典籍中,聖人「如是言」之故,是因為「宗廟世界」,但弟子已經不是站在先秦人倫立場的「宗廟世界」發言,而是想站在程門教學中的當代儒學之立場發言詢問,非血緣的「師弟」之間所傳承出的「道」與宇宙天地間「人」所面對的「世界」之「理」,是否仍然還有「信仰」與「鬼神設教」存在的間隙,---一如後來朱子所為的那樣。伊川師弟間的問答顯然最大的忽略,便是忽略了孔門問答的時代語境仍然是「宗廟世界」的,而伊川師弟的問答則已然越出了此一範圍,更重要的反而是「不具血緣性」的世界,其對「性即理」的思索與探求反而更具普遍與教化的意義。
[29] 錢穆,<中國思想史中的鬼神觀>,《靈魂與心》,頁102-104。.
[30] 黃榦,《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卷16,頁174上。
[31]黃榦,《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復李貫之兵部〉,頁174上-下。
[32] 《禮記注疏》,阮元刻本,<祭統>,頁834-5。
[33]《禮記注疏》,(清)阮元刻本,頁813。
[34] (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1版2刷),卷八,〈宗族〉,頁393。
[35] 任繼昉纂,《釋名匯校》(山東:齊魯書社,2006年11月1版1刷),卷5,〈釋宮室第十七〉,頁285。
[36] 同上註引書,<郊特牲>,頁508。
[37]《禮記注疏》,<坊記>,頁868。
[38]《禮記注疏》,<祭統>,頁835。
[39](漢)班固,《白虎通》(三),附(清)莊述祖輯《白虎通闕文》,(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書》影印),<宗廟> ,頁3。
[40]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卷48,〈吉禮七〉,頁1353。
[41] (唐)杜佑,《通典》,卷48,〈吉禮七〉,頁1353。
[42] 《禮記.曲禮》云: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鄭玄注云:
以孫與祖昭穆同。(阮元刻本《禮記注疏》,卷3,〈曲禮〉上,頁2699)
[43] (宋)黎靖德編,鄭明等校,《朱子語類》(三),卷63,《朱子全書》(第十七冊),頁3044。
[44](清)顧炎武,《日知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9月,《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敬躋堂叢書》本),卷14,238
[45] 《國語》(《四部備要》本),<楚語>,卷18,頁4b。
[46] 《禮記注疏》,(清)阮元刻本,頁831、832。
[47] 同上註引書,頁830。
2009年8月28日 星期五
孔廟的形上學議題
於
晚上9:04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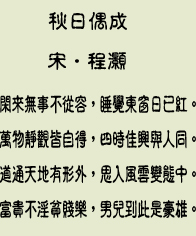
1 意見:
отзывы о электронные сигареты - курение вредит здоровью или алкоголь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