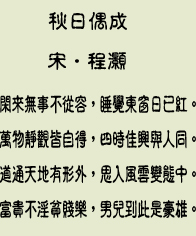坐在Schillers Hans(席勒之家)之前的露天咖啡座感覺真好。
這家咖啡座尚未看到有人點啤酒的,或者是根本不供應啤酒;又或者,是在Schillers Hans的前面,沒有人願意「喝酒」!
Weimar的遊客並不多,比起Heidellberg,少的多了,其中還有泰半是Weimar本身的居民,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懷著享受Weimar與懷著喜愛這個town/country的心情,在黃昏時出來散步,在早晨出來吃早餐。尤其是在席勒的家前。也許不會再有列寧或黨主席的東德。在柏林圍牆成為歷史之後,還要經歷多少時間分裂的世界歷史才會再度共享曾經共同擁有的歷史與文化!正是這種心情!而旅人與遊客,尤其是歐洲人,若知道你來威瑪,總會問一聲:有去看集中營嗎?我不知道我說我沒去或是不怎麼想去,這樣的回答是否會得罪人!但我的確是沒有去,這不是我千里迢迢的目的,我略過一大堆萊茵河畔的城市來此,是想來朝我文學的聖地。如果不知道這東德的小鎮也就算了,又如果不喜愛Goethe、Schiller,怎會來此!因此,Weimar其實不能算是觀光勝地,而毋寧是文化聖地。沒有Goethe,就沒有Weimar;有了Goethe,才有Schiller,才有詩、劇、音樂、文學、藝術。也才有矗立在市中心廣場前歌德與席勒並立的兩尊雕像。還有滿地的銀杏葉。
這次來Weimar體會到的與昔不同,以前只知歌德與席勒是忘年之交,並且還一起創作了許多劇本;在美學上的則有其差異,席勒服膺康德,而歌德則受Herder影響。親近了Weimar,才真正近距離從呼吸中體會歌德與席勒的感情多麼異類,多麼不同凡響!席勒英年早逝,席勒較窮(小康),而歌德是大臣,席勒之家與歌德之家不能相比。喝著coffee,望著席勒,更令人覺得歌德是天才的一生,高而貴,浪漫而正義,才華縱橫,依然令人景仰尊敬。而席勒則此番更有一番較昔更憐惜其的感受。席勒其實只是平民,他的書房,書桌,窗畔,都是一般人也可以得到的;因此,席勒的文學、戲劇及美學上的成就,完全是端看他自己的辛苦努力得來。書房中顯示,他抽煙,肺部不好,歌德在去看他也受不了他房中的燻味。但是簡單的席勒書房還原之擺設,仍然讓人流連良久。而歌德,則真有一番歷史與個人綜合造就此一天才及其時代的意味。荷馬、但丁、歌德,是三大不朽的文學經典巨擘。英國則有莎士比亞,同樣睥睨且傲世傲人!歌德是不朽的!
相較於歌德,席勒卻是後來者可以努力達到的,也因此,這家對望席勒之家的咖啡座就更令人喜愛,無論早晨,午後,黃昏,晚上,銀杏的風味隨風而來;席勒也就更讓人憐疼一些,對他的未享受生活,對他的身體狀況。

我居然來到Weimar了!這對我而言,有一個意義,即我懷有何種情懷,何種懷抱,甚至是一種嚮望,而不是功名;那麼,就有可能醉(浸)在其中,從對星空的仰望到千里外來此,坐在此,坐在座中,在Weimar 的世界中,對著歌德,對著席勒依然是點一杯咖啡,拿起筆,在扎片上寫下我們此刻書寫。海德格之我在此,打開Weimar,迎著其culture而蔽了其他,再也看不見Weimar’s platz及步道與林蔭之外,就是這種存在於此。在此的氛圍與我坐在此的行動,正是一種Da-s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