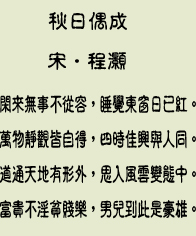李紀祥
——「台灣史學」與外省第二、三代書寫的對話與歧異
台灣史學史?
是的,我決定了。
台灣史學史?你有主體性嗎?你是外省第二代哩!
首先,你讀錯了,是「台灣史學」史,「台灣史學」是我研究的對象,你一定把它設想為台灣的史學界了!不錯,我是一個外省第二代,而且是標準的中國情懷虛構者,不虛構就沒有「我思故我在」的第二代;正因如此,我才特別地站到了一個有利的據點,來寫這個「台灣史學」中的「寫歷史」的現象。
哎!當然,這已經是常識了;「歷史」的生產不一定是在「史學界」,「文學」生產「文學史」,「文學史」研究「文學」史。
因此,「台灣史學」之中,作為文化研究的一環,當外省第二代已經在政權及本土文化的提倡中被淹沒時,一些人的焦慮,就成了書寫這的關注,也就是我所謂的「寫歷史」,因為他們書寫了存在的焦慮、自我的焦慮,——存在即歷史。只是,他們的書寫,不一定是主流文類——歷史類,文類還有「其他」罷?
同時,非主流的選擇,也是你將自己與他們掛上聯繫的主要原因之一?「台灣史學界」與「台灣史學」在你是特別作出了區分的。
因為他們焦慮!
焦慮也有可能來自於「現代化」!我知道你說的是朱天心與駱以軍,特別是四月十日在台灣公共電視台播出的駱以軍專訪那一段,其中談到有關「眷村」逐漸消失的那一段錄影播出。
是的,但是這卻聯繫上了焦慮;而在朱天心與駱以軍的意識中,並沒有將此「消失」之現象聯繫上「現代化」。對我自己而言,作為第二代的外省子弟,受到大一統分裂及中國近現代史述之影響,常不自覺地將知識與求學之責任扛在「中國情結」的肩上;但他們則不同,相對於我,聯繫到了「焦慮」——台灣的存在情境之某種具特別意涵的顯示。因此,他們的書寫,在我看來,更有資格被稱為「台灣的歷史學家」的身份,他們的書寫印跡了存在。只是,這樣的「寫歷史」作為「台灣文化」的一環,是放在不同的文類中上架的。
你說過,對你而言,有利的最根本地帶便是你們同為外省第二、三代。那是否意謂著對「主體」而言,你太牽強而又一廂情願了。不管是「焦慮」還是「有利」,你都已獨占了「外省第二代」這個詞而且居然還不自知;怎知你不是虛構,而又重覆地虛構了「台灣史學」?
是的。但我仍與他們不同,我受到「近代化論述」的影響;而他們,則顯然已有「在地」的身段;在形式上,也較有後現代書寫的訊息;他們以文學作為文類去反思存在,因而已是某一種意義上的「文化研究」。正是在我的主題「台灣史學」上,通過外省第二、三代作一個主軸,我才發現,我自己是第二代,而他們則其實已有第三代的轉換身影。第二、三代間的轉換,也就是通過「史」的視野下所呈現出的「台灣史學」的一種轉換;一種「歷史神話的承擔」、一種「神聖性」,到存在的焦慮、現實性的變化。
這個標題有點長!
你注意到了,標題不長不複雜,怎能清楚述說要表述者呢!其實,這個標題也不完全是我擬的;其中的一組名詞還是借用了現成的文學史版本的。
怎麼說?
王德威將「老靈魂」給了「古都」,「運屍人」則給了「遣悲懷」;同時,「老靈魂」也是聯繫《想我眷村的兄弟》及《古都》的術語,這自然是文學史了。因此我如是說,我是挪用過來的。
你想參與文學史的討論了。
也不全然如此,對我而言,書寫存在的焦慮正是「台灣史學」的一部份,我的目的應在此;你要用「參與文學史」也可以。但在我看來,我已經突顯了「上架」與「分類」的無意義。
既是如此,對「台灣史學」而言,這兩人之書寫分型有何意義?
我想,我直接從「外省第二代之書寫台灣史」出發,從而將之視為這一脈絡的兩位重要人物﹙史家?﹚,並將之分型,就已經是別行途徑,秘響旁聞,不取時下台灣史學界的定義,而直接採取了一種新的視野下的分型。這個分型的意義應當即在於對「書寫自我」就是「寫歷史」的看法之提出,同時分型本身也已經意謂了擺開什麼,同時也進行了什麼!
那麼,「老靈魂」與「運屍人」對你有何作用?
這是一組作為對照兩個作者風格與內涵的語詞,王德威顯然在比較朱天心與駱以軍,尤其是從駱以軍出發,因而倒敘出文學史,述出了一種系譜的轉移:由張大春到駱以軍與由朱天心到駱以軍,有什麼不同及意義。在他看來,「老靈魂」存在於朱天心的書寫當中,靈魂之「老」,正因為老的、苦的可以經歷許多歲月,在歲月的增長及容顏的剝落褪色中,「老靈魂」出現了,以弔古而感傷逝者的姿態。而「運屍人」,則夾縫地存在於九封寄給邱妙津《蒙馬特遺書》的書之間。王德威認為在這九封信之間,「運屍人」的角度最能引起他的注意,因為它梳理了屍身,擺置了屍身;具有特別性!
所以你就挪進標題了。
確然!但「老靈魂」之相呼應於「古都」,「運屍人」之相呼應於「遣悲懷」,你不覺得文學中有點不對襯嗎?
何以言之?
首先,「古都」是呈現了「弔古」,一種屬於「描繪」類型的古蹟式尋禮;而「遣悲懷」則是呈現著「傷逝」,一種主體拋向於已逝者﹙甚至是自己﹚的悲懷之詮釋,九封信之間,全是書寫作為「『傷』逝」之自我書寫,以「遣」其自身之「悲懷」;你不覺得,這和「老靈魂」與「運屍人」剛好呈現出了一組語詞的相反性嗎?「靈魂」之與「古都」的「描繪客體」之指向,與「運屍」之與「遣悲懷」的「抒懷主體」之指向?
是有點對反,「魂」與「古」、「遣」與「屍」;假設你的標題,是意在呈現以「描繪逝者之客體」與「抒懷傷逝者之主體」作為兩類型的話。那麼,「描繪型」就不知是指向「古都」還是「老靈魂」?而「抒懷型」也就不知是指向「運屍人」還是「遣悲懷」了!而且我看你是以「古都」作為「描繪」型、以「遣悲懷」作為「抒懷型」的。
正是,無論是「古都」還是「遣懷」,都是弔古傷逝的書寫,但書名作為一個語言,必須承擔著其所書寫的「主意」,則「古」與「遣」不正好呼應了這兩種弔古/傷逝的不同性!
你覺得用這兩型作為區分以取代之德威的兩型好嗎?作為描繪的「古都」中,難道不是處處可見「遣悲」的「老靈魂」嗎?
我想你也可以問:難道在「遣悲懷」的傷逝中,不見駱以軍之具體地指向了對邱沙津已死﹙及其生前﹚的回應,以及這九封信「之間」的具體指向,就是傷己抒己懷己,而也正就是傷朱天心之所傷者嗎?
這麼一說,不就顛覆了你區分為兩型的意思,兩型既不成其為典型,又何區分之有?
區分形態的意義,倒底是天各一方,各據一地呢?還是藉由分析語言而呈現其型?在我看來,區分為兩型,不正是要這兩型之彼此間相互映照嗎?此型之中有彼,彼型之中有此,因而相互性、合成性就出現了;但在書寫中,畢竟有其限度,此書在此,尚有殘缺;彼書在彼,亦然;但一經分型,彼與此就在文學史的天地間結合。小小的誠品、金石堂,方寸之間,自有可觀姿態!
因此,「古都」之「古」,雖為遺址、遺跡,但卻有個「老靈魂」在其中,否則又怎能述說其泣,如東坡赤壁賦之婦幽與蕭哀;而「運屍人」雖指向「屍」,但駱以軍更在意的,是書名的「傷逝」之「遣悲懷」,自身不遣其存在之悲懷,又怎能弔向於已成古、已往逝的《遺書》中呢?
再進一步說,倘使世界不褪色,容顏不花落,又何來「古」之有呢?川端康成之「傷逝」不也在此。「古都」正是如此地作為「遺址」的「描繪型態」而進入朱天心的「老靈魂」中。然則「古」而「弔古」,「悲懷」亦「喚古」,這個世界,正是因為流逝,才須要書寫,書寫的意義,正在於此;若有盤古能使世界不古、傷者不悲,書寫就不須要書寫者,存在也就不須要焦慮了。
海德格好像說過:存在的焦慮就是一種「畏」,「畏在世界之中」!
大哉斯言,但我不懂你幹嘛要忽然扯進海德格!
………………………………………………………,
………………………………………………………。
這兩位作家,是書寫者嗎?
我知道,也了解了你問話的意思,你又在挑我毛病了;好吧,他們兩位,在我心目中,的確是「作家」,也同樣作為「書寫者」,但卻不具學院內制度化的身份,但我可要指出,學院內的制度仍然是與他們有聯繫的,不管是「作品」還是「作家」自身。
這樣「台灣史學」可以成立了!我想是在任何一個角落,特別是他們的書房,作為一個角落,也正是「台灣史學」發生的場景。不錯,但,「在制度中的台灣史學界」呢?
我就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你終究會回返這個「史學界」,因為「台灣史學史」這個詞彙總是在已然中成了一個癥結,一個閱讀上的影響與情結。那你何不說清楚,「作家」與「台灣史學」倒底是如何聯繫的?其實我已經表述出了,無論是金石堂的上架還是學院圖書館上架,它們都是一種分類的上架——即「書的在世界之中」。
我想:作家以一種不具學院制度中的身份,名器不經國家制度之授予及憑證,應當確實有它那麼一點意義吧!雖然你也已經說了,他們與學院及制度還是存在著聯繫!
我記得有人這麼說過,是比喻罷!畢卡索就像是一只章魚,把觸爪伸向每一個有獨創性的角落,汲取他們的創作成為自己的養份,而成就自大。
剛才你對海德格被我忽然扯進來,好像頗有嘲諷;現在你有幹嘛忽然扯進了畢卡索。
學院制度中有兩種型,一種身份之名是「教授」,一種身份之名是「研究員」,但如果混淆了,就會出現大小章魚。
什麼意思?
大章魚常常作為一種怪獸象徵而存在,王德威的書不就是從「檮杌」而出版了他的《歷史與怪獸》。在「台灣史學界」,原有兩種制度的型態,一種是研究院類型的,其成員叫作「研究員」,所以常常感覺缺少書院中家的師生氣息,於是只好不斷地無意識地將章魚爪伸入大學系所中以求生存,否則,就會覺得缺少了世間的什麼……
你不乾脆說是「名」好了!
不能這麼說!作家不也在「名」中!
別打斷我,「研究員」於是與「教授」發生了一場混淆的文字遊戲,我在網路遊戲上看過,結果是出現了一群大章魚與小章魚。
作家似乎不在這個制度的遊戲之內?
「作家」,基本上與「作官」不同,這是「作家」之所以為「作家」,也是其自寓的「家」之所以成為一家之意!基本上,「作家」確是不是一個可以授証的制度,也應當沒有這個制度!但研究員——教授——作家三者是否有著聯繫,我不認為我能看出什麼,我要說的,還是「作家」。人人都可以是一個「作家」,書寫自我,書寫焦慮,書寫抒懷與觸目所見;作為一個「名」,作家焦慮的是如何升等成為一個真正的「一家之言」,而並沒有制度上的升等為「教授」與「研究員」。因此,「台灣史學」在我看來,還是值得關心的「史學」。
你總算說的清楚了,但也因此而味意盡失。
別諷刺我。「書寫中的真實」因此而變的抽象了,因為作家的「在世界之中」而使得「書寫」一詞變得不真實起來,像是一種哲學上的幻象書寫,追尋著烏托邦、理念,不但把「客體」絕對化,同時「主體」也被概念化、文字化。
史學、文學都有嗎?
當我們把書自「架上」抽下,買/攜回家,自己閱讀在自己的角落時,我們才算真正參與了書寫的世界的構成,「作家」的身份,你不覺得因此總是在這裡被辨識與確認了嗎?
這樣,你所說的相互映照,以及書寫的意義便又重新浮現上來了!
天呀!不就是這樣的嗎!
存在之焦慮的自我書寫,正是「台灣史學」的版圖缺塊,此一缺塊可以自此種類型書寫進場,觀索其軸線,倒不一定要加入過多的作家編年或是身世傳記,類似「年譜」與「傳記」的史部分類。
因此,書寫自我——即外省第二代所居之消逝,就是小敘述了?
正好相反!有了「文學史」,小敘述反而是大傳統,「台灣歷史」由誰執筆,未定正由天,而人亦儘逞其能。「文學史」因而是「文學」?我不這麼認為,有了「文學史」,台灣史學因而注意到書寫自我的存在焦慮,很可能反而成為是見證五十年來台灣作為記憶/歷史的最有意義與指標之處。
你是說,文學反而不成其為台灣史學的邊陲書寫,不是「小說」嗎,九流第十家,巷閭之言,在都城裡?
這麼說吧!〈箕子世家〉之與箕子獻陳武王的〈洪範〉篇章,形成了一個對比:「消逝的殷墟」與「新生的禮樂藍圖」;難怪胡蘭成的「山河歲月」充滿了近代的傷逝與傳統文明建構的筆調,這樣,就把「古都」的系譜從胡蘭成又上溯了;從而,「古都」的場景以及存在的焦慮之歷史意義,也就更能讓我們突破「文學史」一詞的近代性侷限而抵達了朱天心自我撥撩的靈魂深處,她想嘗試的,還是書寫與聯繫一個大格局傳統,通過胡蘭成與箕子的聯繫,我們窺見了這一塊版圖的缺頁。
我覺得很好玩的一點是,王德威竟然會透過金聖嘆而將朱天心的「古都」聯繫上了司馬遷?這很令我對「文學史」的驚訝又多了幾分!
不是「台灣史學」嗎?
說的也是,「虛構的大中國之魂」又出現了。但王德威也有道理啊,胡蘭成不是一個最好的媒介與系譜嗎!就像武俠小說般,胡蘭成作為「文學史」這部小說文本中的「師父」角色,不把「江山懷古」這招傳下才怪!
於是「怨毒」寫作類型的筆觸就從「文學史」出現了?
正是!「古都」兩字究竟是作為「朱天心的」弔古好呢?還是還給她一個「歷史的」胡氏江山系譜好呢?
看一看〈箕子世家〉吧,司馬遷寫的正是「廢墟」呢!廢墟?古都?總督府、「康寧祥」、新公園、西門町、末廣町,以及「千重子」,眷村,傷感?弔亡、懷古?這一切,朱天心果然是一個「寫歷史」的作家。這麼一看,再觀察一下〈古都〉,外省、本省,是不是淡了一些,讓人不禁悠悠又惆悵幾分,在那〈古都〉之下流動的朱天心幽幽筆觸之水?
恐怕不只是「淡」了一下,還多出更多的缺頁在這版圖的缺塊當中。她呈現的,正是「起源」作為「神話」的意義,自我定位的破除、第一位的消解: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雖然據说這是他們東行以來所命名的第十二個美麗之島。
不滿那地方的,不自你始。
天啊難道那幾株橄欖又礙誰惹誰了!你尋它們不著。
消逝了的不只這些……
歷史可以破除「起源」,考古可以深掘,主體性於是逐漸成為形容詞,「命名與起源」的奇魅與神話,蘊藏的寓言這才騰出血來。
因此,廢墟以及面對廢墟,這種相互映寫的場景其實是不斷出現的,生命中每一個段落都可以是這種場景。而描寫抑或是召喚——書寫這種生命的形態也有很多種!例如〈箕子世家〉的本身,就傳達了「司馬遷與箕子」原來在「殷墟」之前是可以重疊的;而近代西方漢學中對於「三代紀年」的「斷代」關懷,把「箕子與武王」的對話,納入其「考訂」之中,也是一種面對;同樣地,「處於其中」的自我書寫,也是一種筆調的歸類;把「三代斷代」及〈箕子世家〉當作是「史學」,以及把〈古都〉當作是「文學」,亦誠然是一種面對,一種面對的態度與類別的聯繫;但有形聯繫的根源都莫不是由無形冒出來而呈現的。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 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果然是一派「廢墟」,在《太史公書》中。這麼說來,「廢墟」當然也能被朱天心寫入〈古都〉中了。
是的!「消逝了的不只這些……」、「不自你始」,說她「寫史」也自是有道理的,歷史是大書寫總是綿綿地藏在歷史的小書寫中,「文學作品」因而成了「名著」,總是見證著歷史的文本化!
若只看〈古都〉的表相文字,就等於是「台灣史學界」寫「台灣史學」似的,朱天心就只是成了「台北史」的「地方志」作者了。
你真是了不得,一語道的!
我可不是外省第二代!
這個「名詞」終究會褪色的。我自己也很「悲」啊,要「遣」!
你不是已有「虛構的大中國」可以玩「虛構情懷」的遊戲了嗎?
可是捷運也很好玩啊!君不見三三一大地震,世界最高大樓﹙未來﹚跨了兩座鷹架,我週末去華納威秀因此而要繞路。
這和遣一遣中國情懷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我要去華納威秀看電影——我還記得小時候在成功新村坐在廣場前看「長江一號」;我哪料到電影在清末曾是「洋片子」,而今卻成了我抹不去的懷古記憶;亦復和「古都」中的青康戲院共同聯線成了老容顏——看完電影後要遁走新光二館的陽台咖啡館,開始寫作;地震造成了災難,交通遭到管制,它擋了我的原來路。我得繞路、換車,從信義路轉松德路、松仁路,耽誤了我寫我中國情懷的時間。
那你寫「在耽誤的路上」好了,反正松德路、松仁路我第一次聽到,對我沒多大意義。
可不是嗎?「歷史」的呈現,端看自我的拋入何方,過去也罷,現在也罷;拋入的狀態倒頭來總要和被拋入糾纏起一份必須理而卻又理不清的情結總帳簿。
那這樣「古都」的路名就顯得有意思了。在「古都」中,你可以注意到,朱天心拼湊的大唐長安或是大隋大興的街道,對她而言,「本土」不經意地常流入她的意識之中,這也正是她自我沖撞與痛苦來源的另一面。你注意,川端康成決不是僅僅以《古都》的文學前輩之姿態,進入她「古都」的篇章書寫與角色佈局中的;細細讀來,一股潺潺的日據時代之遺音氣息,仍然在「胡蘭成時代」之後迴響不已,流經了台大而進入她的世界;西門町啊末廣町,這些街道的反饋與積澱,仍然搖曳了櫻花之姿,化名杜鵑!
那麼,川端康成的影響就不只是文學的姿態出現在她的書寫中了?
正是,文學的姿態之後,還有個身影吧!
是啊!這些街道的名稱,蘭州街、迪化街、溫州街、南京東路、長安東路、安東街、重慶南路、北平東路、青島東路、濟南路,對我而言,路名即是我成長的記憶,烙印著大中國的語境,是如何的在記憶中塑我的形、塑我的心;但對她而言,底下恐怕還有已經被「本土化」了的總督府、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野村一郎的台灣銀行,「啊找到台灣神社了」、「掠過劍潭山腰」;路,對她而言、對我而言,是不同的;我記得的是路名,她掘出傷痕的是「路的歷史」;於是,「林中分歧為兩條路,我選擇旅蹤較稀之逕,未來因而全然改觀。」
你又說了些什麼?
這是〈古都〉中朱天心引用Robert Frost的中譯文鉛體字。
……,……。
所以我說,朱天心的「古都」,正在「描繪」的古都,是一片廢墟,層層的考古穿透了時光,掘出了歷史之旅,在她行旅的腳下。〈箕子世家〉中箕子憑弔殷墟的影子也因此而不斷浮現於我閱讀之過程中。「也有屋子早荒朽成虀粉遭風吹眇只存庭園和圍牆門台。」消逝了的不只這些,消逝、褪色、物換星移;更緊要的是,都還在呀!只是「名詞」改變了!因此,傅柯的「詞與物」形成了「古都」仍在、「古都」曾在、「古都」何在?——的一片茫然。考古的描繪中情境照然,於是老靈魂才能在此、在昔、在今般地來來去去穿越時光,震驚自己。
*我在捷運中翻閱《蒙馬特遺書》,卻見不到「運屍人」來來去去
那麼,說說駱以軍吧!
駱以軍只要搭一趟捷運,就連起了屍旅,「遣懷」出他的「死亡之悲悼」,母子的、外省第二代以及迴向「遺書」之書寫的在與不在之悲與我遣悲;但他雖「遣」,搭的可是「捷運」,完全地現代,完全的今名!駱的筆法,畢竟與朱天心不同,〈運屍人a〉他搭完了捷運,到了頁305〈運屍人b〉,彷彿走出了巴黎的地鐵出口,我們望見了——藍天,不!「他﹙仍然﹚推著母親的輪椅」,「他經過一個有噴泉池的花園」「草坪上有一些小圓葉灌木被修剪支架成長頸鹿、恐龍、山羊或是白兔的形狀。」多麼具像的「描繪」(居然可以分辨長頸鹿和恐龍,山羊不是綿羊),而且那個「有」字,很「有」意思!這些「描繪」之中,才是駱以軍的遣悲懷。顯然駱的描繪,幾乎是一種「堆砌」,與朱天心的一個個打自心底而湧出的名詞都是「曾在」不同。因此,九封書信,反而像是母親的屍體突然地跳出來般,第四書就這麼地從頁89蹦出而躍騰於頁309之前。「在您的遺書中最令我瞿然心驚的那一塊……一次性傷害。」﹙緩緩翻了一頁,頁90﹚
「有太多老傢伙在我們眼前自殺。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早在我們懂得翻開他們的書之前,便已紛紛死去。」
﹙再翻一頁﹚駱必須要搭捷運才能遣出悲懷的字句。「也許必須有一組足夠複雜的動作。」駱的文筆,以及他的筆下,是必須要有隱飾,他才會躍出自己的。「怎麼回事?忍不住想問您。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我」稱「您」,來「遣悲」而「懷往」!像是一黑一白的竹籬,不知道他會藏到那裡,又像是一站又一站的捷運之旅,哪裡又被他藏了一個故事的夾縫,夾縫中又有個敘事!
書上不是說他﹙說﹚是「隔壁」書寫。
正是,他常將自己放置於一個「夾縫」之中,隱藏自己,「隔壁」式的書寫可以讓他顯得更冷靜、感覺更自由,羞怯的眼神個性在文體中安頓好之後,文筆就更自在而益深沉了。
你也陷入了作者與文本的聯繫之中?
那是因為「捷運」指點了我許多事!一種無可阻擋的起伏、澎湃,使駱以軍認真思考自己的系譜,因而以另一種方式回應了邱妙津的遠去、《蒙馬特遺書》之「遺書」的書寫告白;我想,駱以軍正認真思考這個面對,他必須面對這個「自我」的「告白﹙書寫﹚」之震憾,一如卡繆對存在的「異鄉人」及「自殺」的文學、哲學兩途皆須作出回應一樣;總之,寫作,或他,必須面對「自我」的「存在」這一回事,而這也促使他更深沉地看出了朱天心書寫歷史的意義與告白自我的用心。他在作某種巧妙的銜接。「遣悲懷」呵,主角最終還是「自己」!儘管《蒙馬特遺書》已經逝去,身體已經死亡,「她的身體裡某些部分已經死了。」「一個身體的死亡,一旦進入……專業理解,就會出現了好幾組不同的死亡時間。」決定以「書寫」來「悼亡」的是他自己,搭乘捷運扛下「運屍」之責——抒遣此悲乃是天職的,也是他自己;至於份量有多重,廢墟、容顏與花謝、褪色能有多深,就恐非他所能再搭一趟捷運之料想了;畢竟,廢墟與歷史、斷層與地表、逝者與所悲,傷逝者、書寫者,也只能盡其在「自己」。
但是,不管怎麼說,對於一個要遣悲懷而悼逝者而言,書中畢竟還是充滿了「描繪」。
的確是如此,「那具屍體」一直不斷地出現,出現在「他替屍體戴上毛線帽,圍上圍巾。」出現在「就像那些放過了賞味期限的保險膜包的切塊水果,摸摸鼻子便丟進垃圾桶了」之後便又再推起「他母親的屍體」。也出現在那具屍體的「生前」,「生與死之間的清楚界限再哪?」「那些他不在的時光,他母親都在看什麼樣的節目喲?」生前的時光,無論「在」與「不在」,都必須由「那具屍體」來映照,生死之間——生前與死後、逝者與懷逝者,界線便在這裡,這條界限不是分別、不是分判,而是聯繫,是生與死的聯繫,把天人永隔理解成「在/不在」,找尋一條因傷感而模糊的界線,恐怕不如從自身的悼念「生前」於「屍體﹙死後﹚」的「同在/共在」來得更為深沉!因此,哲學思維畢竟還是決定了文學寫作的方向。
但是「運屍人」畢竟有「屍」有「運」、有「生」有「死」,駱的筆法仍然還是成功的。
如果就「生前」與「死後」,則「那具屍體」似乎意義就不只是「尋找一個生死之間清楚的界線」,而應當是「聯繫」起「在」與「不在」,這就是「死亡」告白與書寫的真實意義,每一個人也都可以作到的!我們沒有筆,但我們仍然以「懷念」之姿在書寫我們自身的身體,仍然留下傷逝歲月的刻痕!駱的體會仍然是用著「對比」與「夾縫」隱藏的筆法,「現代的」名詞不斷出現,來對比一個「過去的」時空,因此,「傳達仁」可以很自然的出現在書中;其次,「那具屍體」的「生前」——母親在「松山機場」搭飛機降落的那一段書寫,仍然不斷地運用著「描繪」,描繪「坐飛機」的往昔,隨著穿越生死線——藉用了「憶」﹙還是母親「說」的﹚,不斷地出現這樣的「對比」。也因此,駱也只有用「描繪」來運用「現代名詞」——或者是「過去名詞」。否則,就會形成生死一體,不成其「象徵/描繪」式的「遣悲懷」,以及「生」與「死」的對比了。貫穿其間的,仍然是「憶」的種種在作用我們的人生,過去、死亡、遺書、遺留、現在、映照、映入眼簾的,都可以解釋成駱以軍的風格。過去,留下的不過是一具手推著的「那具屍體」,還是「母親」?向「死亡」的「您」哀悼,還是「遺書」?
因此,駱註定了必須要描繪,也就是一定要讓「那具屍體」來一趟「捷運之旅」,否則,駱的「遣悲懷」與「死亡之舞」的主題之冒出,與「屍」之對話,母親與身體之生死之旅的穿越與駱本身身體記憶的蘊藏,就既不能自「夾縫」中冒出,也不能自「隔壁」傳來聲音。
但是,「隔壁」傳來的淺淺地悲,畢竟到達了終站!
人總要到達那條對街的!下雨了。
……。
二○○二年五月廿五日初稿
六月八日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