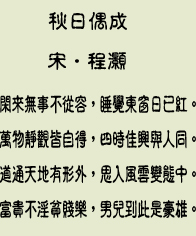歷史上的京畿觀與天下觀
一、大陸形勢天下觀中的長安與燕京
中國歷史上,向有五大古都之稱,此即:長安、洛陽、汴京、燕京、金陵。吾師王恢先生為近代史地名家,曾為錢穆《國史大綱》及《清史稿校注》中手繪輿圖,圖中蠅頭小字皆出其親筆。其所著《中國歷史地理》上冊,即以秦漢長城、唐宋元明運河、及歷代之五大古都作為表述之重點,至下冊方為歷代州域建置之沿革。於五大古都篇中,對於吾國歷史上的南遷與西播、長安之大陸形勢、燕京之海洋形勢,尤三致意焉。
清初遺民顧炎武,晚年居於關中,顧氏為江蘇昆山人,其所以居西北,審度天下形勢以待變可以有為也。可見顧炎武對於關中形勢與天下的觀點。這與另一清初大儒黃宗羲晚年隱居浙東著述其《明夷待訪錄》正相反,黃宗羲對於定天下京師的觀點係主張定於金陵的。
顧炎武並著有《歷代帝王宅京記》,自三代以來之歷代都城之有關史書之記皆摘入其中,乃知係一有為之書。惟顧氏雖然對於京師所在有所留意,然於天下形勢分析,則少着墨。對此補其闕憾者,則當推另一遺民顧祖禹。這兩位顧氏,就是被錢穆太老師推許為「少時慕吾鄉二顧之為人」激勵其少時即有學問之志者。事實上,不論是顧祖禹還是顧亭林,抑或是錢穆本人,對於首都的主張,皆是推重立於關中形勢建都為朝的長安時代。如此看來,歷代知識分子對於建朝立都,還是有其一貫的關懷。錢穆後來在抗日戰爭末期首先撰文討論戰後的新首都問題,不能說是沒有其歷史上的繼承。
顧祖禹的名著為《讀史方輿紀要》,此書之絕倫,魏禧稱它是「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作者則自稱此書為「以一代之方輿,發四千餘年之形勢,治亂興亡,於此判焉」,這也可見他的自負了。我們且看他對全書一百三十卷的篇章結構:
首以歷代州域形勢,先考鏡也;次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東、山西,為京室夾輔也;次以河南、陜西,重形勝也;次以四川、湖廣,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東南財賦所聚也;次以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自北而南,聲教所為遠暨也。
在這個佈局的說明中,我們還看不出來顧氏所論的天下形勢與京師建都之關係。但其書以《歷代州域形勢》為開卷,表示他非常重視「形勢」,他說:「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勢出於其間矣。」專論形勢中,對於建都之所尤其再三諄諄致意。他在〈北直隸形勢〉中本當專門論「北直隸」的形勢,卻筆鋒一轉而論到關中去了。他說道:
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隸乎!
然則建都當何如?曰:法成周而紹漢、唐,吾知其必在關中矣。
在問答中,他直指他心目中的理想建都之首選在於關中。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如果從國都的所在來論,則實可以分為兩個大階段:一為關中的長安時代,舉凡周、秦、漢、隋、唐,都是都於關中的長安時代;一為燕京,遼、金、元、明、清都可算是燕京的時代。而居於長安與燕京之間的洛陽與汴京,都於此者,則有東漢、北魏孝文帝;都於汴京者則主要是五代與北宋。可見洛陽與汴京正是在長安與燕京時代形勢東移的過渡。顧祖禹形容關中的形勢曰:「以陜西而發難者,雖微必大,雖弱必強,不為天下雄,則為天下禍。」睽諸歷史,商代亡於八百里之岐周文王與武王;而周都鎬京,遂成其八百年基業;戰國時東方八千里之六國,而一統於千里之秦國;漢初高祖納婁敬與張良之言,敢於以關中為都;而項羽則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然漢初都長安並非安逸,匈奴雄踞北方朔漠,後遂有平城之危,賴陳平奇計方得轉安。中國大患在北方與西北,是故長安不僅是中國域內之首都,同時也是整個政府有其進取的開國氣象之展現。隋唐代何嘗不然,隋文帝於開國之初平陳之役後,即着手規畫歷經南北朝殘破已久的長安新城,曰大興。隋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惟有李淵父子自太原入長安,此時長安早已殘破,然李淵遂以此而定天下。同時,唐太宗雖亦如漢代般有稱臣於突厥之恥,而終於擊破突厥,成就其天可汗之天下大業。不論古時候的匈奴、突厥,還是近代以來的帝俄與蘇俄,都是北方的大帝國,然而,匈奴衰而大漢起;突厥裂而大唐興;是故近代具有文化情懷的史學家陳寅恪在數十年前寫過一篇〈李唐父子稱臣突厥考〉,正是隱微地指向中國與莫斯科的關係,可以有變,而亦事在人為,審度形勢與歷史關係,不愧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方今俄國形勢已變,整個歐亞大陸的形勢也跟著起了莫大的變化,與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初起的時代士人們所感受認知到的海上起風雲的新時代局勢又大不同矣!則長安每每在殘迫之後還能夠再興起一個盛世時代,當有其形勢上的必然性矣!不僅是一個對內的京師上選;而在對外方面,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進取有為的大時代之首都。
凡以長安為都者,洛陽則必為其東都;若長安為一政治與軍事中心,則在古代,洛陽則為其文化中心。洛陽古稱中州、中原,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一向為中國華夏文化之代表地。這種東西對峙的態勢,要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亂以後,才有了一次絕大的轉變,成為此下長達近千年的燕京時代之來臨。這一形勢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運河,南糧北運,不知不覺中大運河的航道逐漸東移,這就是元明清時代運河貫穿南北以北京與杭州為兩端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燕雲十六州---幽燕地區的落於北方民族之手。從此,燕雲形成為北方民族深入中國的一塊形勢要地。只要敢於居此,便可以當開拓之前端鋒勢,拓其大有為之向外開拓。這是北方民族向南方中國的形勢。而燕京正是在此一草原民族向南征伐中國的形勢中所凝聚出的上選都城。換言之,燕京對契丹、女真、蒙古而言,就正如長安之於漢民族,象徵著對南方開拓與對外的形勢進取與有為。燕京時代的來臨,標誌著北方草原民族征伐南方農業民族所孕育出的燕京之地位。但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燕京的優勢常在北方與南方對峙的時代,所以在歷史上,燕京是一個具有對內統一性格的京師首選之地;這一點,無論從契丹之威脅北宋成為當時亞洲世界的盟主,或是由金代之威脅南宋退守至半璧江山,或是蒙古根本就滅了南宋而在中國建立了元朝,就可以看出幽燕地區成就燕京之為北方局面的特性。一旦京師上選從長安移轉到燕京,中國北方南下一統南方的路線也有了變化。長安時代必定是先取長江上游之川蜀,而後沿巴東順江而下,下武漢而取南京,如西晉之平吳、隋之平陳與宋之平南唐;到了燕京時代,則直接自山東、蘇淮之地而南下渡江,是一最為捷迅之路線。從古時的金兵南下追南宋高宗到近代的淮海戰役,歷史上的地勢還是影響著創業與守成或是開一時代之新局的!因此,如果一個時代已經大一統時,燕京是否仍然是一個對外進取的京師上選呢?顧祖禹顯然沒有討論到這個課題,同時也沒有將海洋的世界形勢納入來考量與思索。顧祖禹所描寫的形勢,畢竟只是中國的「歷代州域形勢」,而不是「包含了海洋時代之後的域外萬國之世界形勢」。清代初年之時,對於這些遺民而言,利瑪竇的五大洲之世界新圖《山海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早已自明萬曆以來已傳佈於中國域內;但顧祖禹顯然沒有受到這些耶蘇會士攜來的世界新圖五大洲形勢的影響。我們從顧氏該書的〈凡例〉界定「方輿」一詞的定義: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
就可以知道他所持的仍是傳統上的「地方說」;但利瑪竇在華所繪製的五大洲世界新圖(從《山海輿地全圖》到《坤輿萬國全圖》)的最大特色與基礎,就在於它的「地圓說」。「地圓說」的重要意義在於改變了世界各大陸地之間的交通方式;我們知道,正是因為地圓觀念的接受與相信,才啟動的歐洲人麥哲倫等從海上開始「環游」世界,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紀---海洋世界觀的到來,也刺激了中國。這個藍色海洋文化與黃色大陸文化的交互碰撞與交流,使得中國人開始將自己視為「五大洲」的「萬國」之一;也刺激中國人在定天下之都與世界版圖的視野上有了轉變。海洋文明的思維全然未受到空中交通的發展而受到影響。只是,在建國之後的今日,甚麼是定天下之中以為京師,甚麼又是京師為國之首都、是環顧天下與世界的視野中心呢?古人所重視的建都立朝的問題與關懷,是不會因為近世海洋世界時代的到來而轉變的,我們依然要面對海洋時代的中國首都的環中以顧天下的課題!同時,中國本身的向來所具的「禹貢九州」模式的大陸形勢,及其在更廣大的海上世界之中的形勢,要如何重新作出新舊激盪之後的考慮與思量,也不能不是一個傳統的一貫議題。知識分子在此仍然應當有著承舊啟新的讀書思惟。
二、「燕京」之為京畿能否兼容大陸與海洋觀點
新時代的天下觀與華人文化版圖
顧祖禹的這部書之弱點在於對宋元以來興起於南方的海洋形勢的着墨較少,同時對於明季以來流傳刊佈的利瑪竇世界新地圖也未受其影響。因此,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顧氏所言者實為「中國形勢」而非「世界形勢」。這一脈絡,代表的剛好是中國南方自宋元明以來的海洋形勢與海洋觀點。將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從西北的傳統陸上西域交通拉向了東南與西南的大小西洋的海上交通。西北的陸路黃沙滾滾,而南方的海路則波濤洶湧;西出陽關的琵琶胡曲轉成了藍色的奏鳴樂章,沿海的形勢成了一八四二年以來中國的發展主線。誰也沒能在明末萬曆的時代中預見到未來:世界版圖的方位觀,到今日為止,已經被利瑪竇模式的《坤輿萬國全圖》的方位觀所取代。
在明代萬曆年與清代雍乾年間,各有一本甚為著名但已為今日人所忘卻的《東西洋考》與《海國見聞錄》,尤其是後者,「海國」一詞的語彙便係由此崁入了魏源的《海國圖志》之中。這兩本書分別代表著明清兩代中國南方所形成的海洋觀點。這種海洋觀的世界之方位,雖然與當時居於主流的大陸型世界觀相同,都是以中國自身為中心;但是,就中國自身的南方、北方而言,仍然有著小不同;而小不同也就顯示出了大不同乃至於衝突與差異。以中國的長江為界,立足於北方,則長江以南便是中國的南方---江南江南,暮春三月草長,便是由北方來的方位稱呼。那麼,福建以南的沿海甚至是鄭和「下西洋」,就更是南方的南南方了;距離黃河流域的北方,感覺上更是遙遠,這正是大陸型的世界觀特色:海洋上的世界,總是一個「他者」,黃土高原的故鄉感受,是土地的。但如果是立足於長江以南,最好是愈接近沿海的浙閩廣瓊島,則由這裏出海航向海洋的大世界時,漂盪在海上這一片廣大遼闊中的一艘艘船舶中時,世界的中心,仍然還是在長江的北方嗎?我看未必!此時對於海上船民那怕是移民也罷,世界的中心應當是在迴望的家園、南方的土地上;這也就是說,海洋世界在中國歷史上是從南方開始聯繫的。立足於中國來統一南北方的海洋之世界觀,必須要從東西南北洋來稱呼與感受這近代新世界的方位認知。處在你右方的,是「東洋」,向左則為「小西洋」與「大小西洋」,小西洋就是今天的印度洋。至於地圖上處於亞洲東邊方位的南北美洲,在利瑪竇尚未登陸上澳門時,他手上的那幅由歐洲攜來的奧特里烏斯的新世界地圖上,美洲的位置是被繪製在世界全圖的左半邊,也就是西半球,那是因為利瑪竇的家鄉意大利與西歐皆處在這幅世界地圖的中心線上;而中國與亞洲則在地圖的東半球的東方邊緣處。到了利瑪竇登上澳門抵達肇慶之後的第二年,一幅有著漢文標注與圖解的最新中文版世界地圖問世了,在這幅地圖上,中國被利瑪竇移到了世界地圖的中心線附近,歐洲與亞洲大陸都是位在這幅新地圖的西半球處---也就是歐亞大陸。而美洲呢?正好相反,被移到了地圖的東半球。如此一來,美洲的方位便移到了中國的右方也就是東邊。但是在清代魏源的《海國圖志》書中,則顯然並沒有追隨這幅利瑪竇為中國人所繪製的世界第一幅漢文世界地圖的傳統;他採用的是西方的傳統:美洲在歐洲的西方。魏源是以向於更為遙遠的西方瞭望美洲而稱它的方位所在為「外大西洋」;完全不同於今日的航空器飛向美洲直線飛行的方向: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美國乃處於中國的東方航線之位置,中間所相隔的乃是太平洋,在明清時代則稱之為大明海、大清海或大寧海。但在魏源那裏,卻是向西而行的「外大西洋」。可見即便是以中土來環顧十七八九世紀以來以海洋世界為主的天下觀,方位與形勢間也已經有了不知不覺的變化,在我們的生活中產生。這樣的方位改變,暗示著世界局勢的若干變化,隱喻著方位觀的移動于天下間便正是顧祖禹所謂的「形勢」之勢異形移。
晚近的若干日本學人在反省二戰以前的日本學界之東西洋觀與東亞共榮圈的論述時,除了希望擺脫二戰戰後日本在亞洲的位所的一片空白之外,也希望從新的反省與歷史回顧之走向中,為日本作一重新定位:既非西方的日本,也非東亞的日本,而是將其皆視為可以討論的論題。日本學界中慣用的「東洋」與「西洋」,其實骨子裏正是對於明代以來興起的新海洋版圖觀及其用語的繼承。將歐美視野中所謂的「東亞」稱之為「東洋」,含蓋了中國、日本、韓國等,「西洋」則稱指近代以來東西方碰撞之後的歐美列國;這種新世界觀的「東西洋」之二分,其實在晚清以降被中國留日的學人與革新份子所接收,遂造成近代以來迄於現代的許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專家,認為中國許多世界觀多是由日本所轉口輸入。然而,影響的源頭,不正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已經出現了的「東西洋」觀與海洋觀麼!日本學者的反思,從丸山真男、溝口雄三到濱下武志等,仍然顯示他們對於日本是一個海島國家的向南洋延伸至蘇門答臘熱帶地域的歷史性,這種反思頗能投入西方學術界的對話之中,香港及星加坡的中國學者們也有這種海洋性格的屬性。但是,他們卻都忽略了一個對世界皆有影響的大事件,這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出現於黃土高原、黃河流域視域中的北方大陸,一個如匈奴、突厥般領土橫亙歐亞大陸的草原民族屬性之帝國,你很難用現代語言如冷戰、國際現勢來解釋這一事件之後的歷史縱深意義---有關蘇聯帝國的殞落的事件。於是乎,一八四二年鴉片戰後以來的中國歷史走到了一個分水嶺:海洋世界與大陸世界的如何重新分型認知,如何能使中國的世界與天下觀是一個既有歷史的縱深、又能兼顧南北方所反映的海洋與大陸世界觀,融鑄於一個最恰當合適的京師、京畿所在的中國之中。
三、一個歷史議題的拋出
當歷史上曾經存在的課題進入現代情境時,它能否仍是一有意義的議題呢!如果以傳統的大陸觀而言,京畿的上選當然是古昔的長安,長安曾在秦末、南北朝、隋末皆遭殘迫,繼之者漢、隋、唐皆能致其復興而復又以為京畿之地。直至契丹王朝時燕雲形勢一變,反成為北方民族之南進基地,究變此一大勢,遂知釀就燕京之為都城氣候數百年之因,此所以陳寅恪先生必獻深刻微言與學術觀點,亟言「安史之亂」與此下南北形勢與華夷升降變化之幾;而安、史正起於幽燕。長安時代之平南,皆自川蜀上游而下江;燕京時代則平南必以幽燕望江,故自魯、淮而渡江以下金陵;京畿不同,其南北形勢之觀亦不同。謂長安與燕京與中國之大一統孰為勝孰為上選,似正為一「大可討論也」之課題,也是議論大陸型世界觀與海洋型世界觀分歧與孰重的焦點,這是過去所沒有意識到與討論到的一個攸關開國格局的議題!
中國自古大患皆自北方起,反之則匈奴衰而漢興、突厥蹶而唐蔚;方今之天下形勢,北方又一帝國衰矣,俄羅斯一旦非北方盟主,中國通西域以聯歐洲之勢將如古昔般復可預見,則以歐亞大陸為世界之中心而言,西北之通與京畿大陸觀之再起,長安時代盛世之象似已將來臨矣。
然而,往昔之燕京,皆為遼金元向南之根據地,否則即為中國域內分裂時代北方以制南方之上選。無論清廷初起之制南明,民初袁世凱之挾北洋以制武漢與南京,或是國共戰爭時期之北與南,皆有以憑藉此一古來之燕京制南形勢。是故燕京者,以北制南之上選也。若大其一統時代業已將臨於中國,天下紛紛目光向內之形勢已將一變而投向外部之際,紫氣東來,又將若何以視?何種京畿方是最為適合未來之天下觀與世界觀,並以教育未來子、民呢?設若中國統一的時代已經行將來臨,則依春秋公羊傳所云,「大其一統也」的傳文強調「一」與「統」之「大」者數端,除改制、繼聖王之統、依農時頒正朔新曆、正其始以布新政外,尚有京畿之為何地以立百年基業的課題。近世以來,中國不論鴉片戰爭以前或在其以後,皆已可見中之尚須有海洋之世界觀及其文化版圖之視野,以瞭望南洋世界與東西洋世界。此一京畿為中國之中樞,則何處京畿可以提供此一既具大陸觀又具海洋觀?以北京而論,自古燕京為北騎制南之地;然近代以來,北平天津與大沽洋沽聯繫海岸為一線,北京即以此而相接海上,是故留學生歸國,凡由船舶以回,必先自天津上岸,故學成歸國者常先為天津之南開大學所聘者,即以此;此可證北京實有與海、與洋世界聯繫之地理意義。然而,海派之風潮又何以常屬之上海,北京反倒充滿著「故都」懷舊之風?若然,海洋世界之風會似又應當係薈萃於此一吳淞、黃埔兩江之近代緣洋而方興之上海方是?上海與北京之風確有不同。看來,北京似乎仍以陸上京畿形勝為多,故其歷史氛圍中,仍多遼金元明清之風而少古昔所謂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時代之風韻,則成其為北京之京畿者,似仍在其近古之勢而不在海上開新運之世也。若然,大一統時代中國之京畿觀,究竟何處可開一代之氣運,合千年之大陸天下觀與近世之海洋觀,以屹立於當今與未來之世界乎!這也就是百年前的經學才子智士---既飽讀經史之籍也讀覽利瑪竇以下西洋新書的魏源在其《海國圖志》之<後敘>中所吐露的心聲:「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有著合西北之陸與東南之洋於一勢的天下觀之關心與期待。
在民國23年即1934年時,錢穆先生首次思考到了抗日戰爭之後未來首都的可能問題,而拋出了一篇廣泛引起學界討論的文章:〈戰後新首都問題〉。錢先生在文中所主張的自是立都於關中為勝;但當時的學者也持有許多不同的論點,各人也都有其各自的歷史依據;有主張北京者、有主張武漢者、亦有主張蘭州、主張南京,甚至主張廣州、上海者;在當時的確掀起一股波瀾,為戰後可能到來的新局勢注入一新氣象。錢穆先生不愧是能讀書的中國人。中國的憲法與美國不同,美國的憲法中規定了首都所在,而當年的五五憲草中則沒有明文的規定。時間推移到1949年之後的台北,我的老師王恢先生在張其昀先生創辦的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系中任教,開設中國歷史地理的課程,他在課堂所明確地主張者,乃是持「北京說」,關鍵便是在於天下形勢當在海洋。當年也許王恢老師沒有能夠料到後來歷史的發展居然會向傳統、向北方大陸變化與推移,沒能料到後來世界冷戰的局勢,是俄羅斯蘇維埃帝國的崩潰,這個崩潰的變化使我們看到了古代漢唐歷史上匈奴與突厥帝國的興起以及其崩裂的聯繫。再一次,我們看到了比漢代西域與唐代安西都護府還要廣闊的西北的歐亞大陸的天際,從北京可以穿過西安、蘭州、烏魯木齊而直達莫斯科而後連接上東歐、中歐、北歐,或是微向南方而與土耳其的伊思坦堡作出整個歐亞大陸的遼闊視域,並以此視野為腹地,來面向海洋世界。這樣的視野,於是與海洋世界形成一種擷抗;是大陸型的長安時代與海洋型的北京時代之孰為京師上選的兩難難境與擷抗;這種擷抗意謂著對於變化的必須思惟,對於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傳統與現代對立的舊型思維的再思惟,一次能融、能蓄、能兼南北、能合大陸與海洋而體現于京畿天下觀上的文化視野之思惟。
從古到今,兩千年史,也不過是五大古都而已,但金陵雖有王氣,但通常多為偏安之局,東吳與六朝已經給我們夠多的啟示;南北隔著一條長江而有長達數百年的南北朝,其惟一的好處便是在相互爭正統、爭勝中造就了不少人才,像原屬南方的庾信在出使北朝後便因北朝惜才而滯居,遂有懷鄉的千古名文《哀江南賦》之作。洛陽則為中原之文化古都,汴京乃是運河與南北氣運升降所一時造成;名雖曰五大,而實則論其朝代亦不過周秦漢隋唐與遼金元明清兩個大時代而已,以京師言則薈萃於長安與燕京。長安是歷史上大陸型世界形勢的中國京畿之上選,燕京則是大陸形勢中國相峙域外尤其是北方時的北伐南之對內一統之上選。近世以來,不惟海運大開,醞成海洋萬國之世紀,同時又佐以航空之古代所不能想見之世。則所謂世界局勢中之通大小西洋,究竟是以陸路通歐洲?抑或是當以海域視西洋?又近百年來之南洋,已為東西交通薈萃之地,此一歷史形勢又當如何納入中國之京畿所在的眺望世界之中,來建構自我的何謂中國與何謂處在世界之中的中國呢!我們在今日可以對歷史有所選擇,或者是對歷史作出不同而又更有智慧的版本選擇,例如:選擇繼承三五百年前的祖先之海洋世界觀;或是,繼續選擇繼承五四時代人面向西方對近世「西洋」歐陸的海洋世界版圖觀的選擇;都是一種選擇。然而,至少在我們在今日決定選擇何種版本的歷史以面對子孫的教育之前,應當對於某種版本所提供的眼界之聯繫應當先作出時代的自覺與反省;以及是否有其他更為開闊健康的歷史之版本。這似乎應當是面對後代的態度。
筆者撰本文、拋議題,不過是效法于太老師錢穆先生之塵尾後,以磚引金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