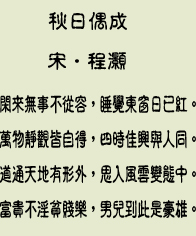容顏所示與容顏敘事
李 紀 祥
李 紀 祥
寒假二月間至上海,閒來無事,至常德路尋訪張愛玲故處,然人世變遷,已不復能游,容顏無處可想,意甚不樂,以文抒懷。
一、觀照---向巴特(Roland Barthes)致敬
1.1 巴特,頁1211
「我看到的這個東西曾經在那裡,在無限與那個人(攝影師或看照相的人)之間的地方存在過,它曾經在那裡存在過,但很快就被隔開了。」(引文中點號為筆者所加)
巴特說的是「面對面/遭遇」與「轉向/不在」。因為,「容顏」的出現,正是「現」於我與之面對面之時,可以將「面對面」比擬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遭遇」,或是一種「凝視」,也可以是巴特的「關心的攝影」。在「遭遇」中,與我面對、被我凝視的「畫面」,成了「容顏所示」,這個對面的「容顏」其「示」了什麼呢?這就要看我的敘事了,但這個敘事如果只是「我的感官、感覺、印象」之單純化,那就是單方面的,我並沒有真正進入這個容顏所示之中。「示」是在我與容顏遭遇與面對面時,把"我-容顏"「之間」的「距離」化為「我與容顏共享的一個空間」,一起構成了「我們的世界」,這才能是對我而言,「對面者」能稱之為「容顏」,而此「容顏」也向我投來「容顏所示」。我把我在「示」中感受到的表達出來,就成了「容顏敘事」。
1.2 巴特,頁103
「我母親在有我之前生活的那個時代,對我來說,就是“歷史”...。我自身永遠不可能有任何回想使我瞥見那個時代,...然而,......我卻能使我身上的一些東西甦醒。」
面對著這樣的一幅畫面:
紅薔薇蔓延上了教堂的灰石牆。(2004年2月2日,上海,徐家匯區)
這一幅畫面如何能在我筆下而產生「容顏敘事」而迴向「那遭遇時存在」,現在已「轉向」而不再了的「過去」狀態之「容顏所示」及「示」中的「我與容顏」呢?我說:紅薔薇在我遭遇它之前,已經蔓延了一公尺又五十公分(假設如此,我沒有親自量過,我也不會帶尺去悠閒地散步!),這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切割成四分之一(春天時節)可以蔓延二十五公分,它已經有了「1年又365 1/4 × 1/2」的「歷史」,「歷史」的長度是蔓延的長度。我不曾接觸過「現在」之前的任何「紅薔薇與灰石牆」的「歷史」;然而,必定是那「歷史」造就了「現在」的狀態。因而,「容顏所示」便可以是「紅薔薇-灰石牆」的「畫面」向我「示」出了「迄於現在」。有某種生命向度以「歷史」狀態而呈現/蘊藏在「示」中,我也是如此的在「示」中。同樣,我來之前也有「歷史」,但這「歷史中的我」終未曾與「容顏」遭遇過。但是現在,「歷史的我」於「現在」來到了此一石牆之前,看到了這一幅畫面,畫面與我面對面著,「容顏所示」,在「示」中,我們面對面、我們遭遇,我們一起共在「示」中,也一起共享與共品味著彼此的「歷史」之來到此。我於是「容顏敘事」,由「現在」在咖啡館中的時刻(2004年2月2日午後上海衡山路上的凱文咖啡屋),正在寫作。已轉向寫作的我,可知:『我現在在此「容顏敘事」』已成了一個「事件」,而在「敘事」中的「容顏所示」,更是一個方才的「歷史事件」,我意圖在「敘事」中寫下「容顏所示」。更進而,在「敘事」中具有歷史意涵的「容顏所示」之中,也有著「我與容顏/紅薔薇蔓爬在教堂灰色石牆上」的「各自歷史」的「來會」,在「我」與「容顏」之「遭遇」中。
1.3 巴特 , 頁107
「我獨自一人去了她過逝時住的房間,想找到我曾經愛過的那張真實的臉。結果,我找到了。我母親那時五歲(1898),她哥哥七歲。」
「我 "知道"那是她,但我 "看不見" 她的容貌:(不過,作夢的時候 " 看得見" 嗎? "知道' 嗎?) 我夢到她,我夢到的又不是她。」(巴特,頁105)
在「容顏敘事」裏,你「看不見」書寫(敘事)者的「方才」。在面對面之際,相互所示的「容顏」,你「看得見」嗎?你只能憑想像來聯結「敘事-所示」,你只能憑「閱讀」進入「敘事」去尋找書寫下的「容顏所示」。「容顏敘事」能再現「容顏所示」嗎?你的目光貼上「文本」之際,--也是一種在目光中的「容顏所示」,「看得見」的、或「看不見」的。在「文本」中的「容顏敘事」,不正在你「閱讀之際」已轉成了與你遭遇與你面對面的「容顏所示」麼!自然,你閱讀的仍是書寫的「容顏敘事」,你閱讀到什麼「敘事」中的「容顏所示」呢?還是你不再追尋,只是在咖啡館中閱讀,盯盯的凝視,從「容顏所示」轉成而來的「容顏敘事」之「敘事文本」,在咖啡館中只是一個「文本」,與你相對、與你遭遇,你的閱讀你的書,你在桌上手持咖啡色書皮的書時,眼與書中之字的距離,與週遭的咖啡香所能飄及之處,加上窗外的天際與陽光反射,一起構成相對之際的「容顏所示」,「書」便是你的「容顏」。旁座也許有人正在觀看這一個事件,對他而言,只要他或她「經意 / 凝視」,你的觀看閱讀你的書,你們的「容顏」,對他或她而言就是另一個「容顏所示」。
1.4 巴特 ,頁108
我仔細觀察那個小姑娘,終于在她身上又見到了我母親的影子。
在我母親生活的最後階段,就在我看它的照片並發現在暖房裏拍攝的那張照片之前不久,她已經衰弱了,已經十分衰弱了。我一直陪著她。......對我來說,她成了小女孩了,跟她那第一張照片上那個小女孩在實質上合為一體了。(頁113)
巴特看到照片中的少女,是他的母親,在他出生之前。這是什麼「容顏入目」!我怎能看到在我出生之前母親的少女模樣!那樣清純的辮子般!但是,這照片卻已經很老了,比我還要「老」。那是在我母親之為少女時--照片之中的--「誕生」的照片。因此,我此刻「持」在手中的,不僅是「照片之中」的少女,也更是將「照片之中」含在其中的一張有邊框的「照片」。我將目光些許退後時,便看到「它」的邊框,有邊框的並且含著「照片之中的少女」的「那一張照片」。此刻,與我面對的,不僅是「照片之中」的少女,而且也是「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顯然比我「老」,昭示了「照片之中」的少女可以比我「老」--是我的母親在少女模樣時攝下的「痕」。那「痕」,依存在「照片之中」,也是比我「老」!只是與我目光相對令我呆呆怔忡住的,仍是那「十七歲般少女模樣」的「清純」吸引著我的「我的母親在少女時候的模樣」,藉著我手上「持」著的「遺跡」,我與其「之中的容顏」相對相視而相示。於是,照片向我召喚,召喚我的目光相對而「示其容顏」,我於是乎寫下這一段「容顏敘事」,邊思索著方才的「容顏所示」及其感動!
二、西安城牆
1.遊記
由是,西安城牆可以述說由漢代至明代長安之「城牆敘事」,以其城牆之容顏座落而在夕陽餘暉映照中之「示」而「說出」,有待我們前去觀「示」而「敘事」,轉成為「文本」之形態。以下是一篇遊客欲訪西安明城牆的遊記:
昨晨清雨,城牆朦朧,雲蔽日故未登樓。今日黃昏,視野尚佳,燈華已上,牆外有聲,是秦腔嘈嘈。獨自行走於城上之行道,此行道甚寬,可供人騎單車,亦有小型機動車出租。此時月華破雲而出,銀白照映城牆,青階皆石,鐘樓皆木,略黯沉斑剝已有年歲之黑顏,彷彿訴說低語,並向我哀沉注視。此時此刻、來此在者,正是旅人凝入西安城牆座落之中時。一切緣,來自夕照木紋斑剝,月映青石城階,與夫旅人一人獨自之行,想像李白「長安一片月」,想像平陽公主正轉身回眸,那長安人家,小樓閣欞,青衫尋常亦復嫣然。我有感,我遂面對,與城牆面對,融入城牆及其週遭市集,一切高樓摩登皆視不見。此時,只有漢唐長安想像能入我心,我視城牆座落為容顏,料容顏示我應如是。
若我無感,若此際無月華,若月華不銀白,則城牆亦只是城牆,而遂無容顏向我召喚,容顏所示,即是:城牆座落與旅人行來立佇所面對而共在之世。我既無感,城牆亦復只是城牆,座落仍舊千古,自隨年月而歲歲更老去,自自在在(孰知?)也不復有面對者,也無遭遇,也無容顏。
若我無興無趣,或今日正霪雨霏霏,遂無與城牆際遇之機,便無此時此刻、旅人與城牆共有之對面。緣乎昨日,是霪雨且霧矇,我遂無立姿之可能。只有轉向,以背影向城牆,旅人正面迎向一輛駛來之公交車,驅往大雁塔尋雨中雁影。
在這篇遊記中,有幾個關鍵詞足以作為術語般的注意:
- 面對與遭遇---相遇方有相視,相視方有此時此刻之所「示」
- 我來此,我在此。
- 轉向---即是「不面對」。不面對又不是不存在,而是行動者已轉向面對它者。只是文本敘事不以此為主題 不以是為主角 不以此為聚焦 遂若不在敘事之內。故「城牆敘事」因天氣不成,轉向大雁塔時,即為城牆敘事情節之終了;然就大雁塔而言,敘事才正開始。
2.「明城牆」的座落與容顏敘事
明城牆座落在西安。 是「物」嗎?是「城牆」嗎?是已經持存了四百年的「明城牆」嗎?即便是「明城牆」,它的現存意義,或是它所呈示的「自身所示」之意義是什麼呢? 「明城牆」之「明」,在今日 / 現在已為民國或共和國之時,「明」已然是一個「歷史名詞」,因而「明城牆」必然也是民國 / 共和國的現在仍然「活著」的一座城牆,座落在西安,--不,應當是由長安至西安,活得已夠老,逐漸高齡且老去的一座「明城牆」。就今天而言,它顯然已經是一個「遺民」了!如果我們來「西安」就為了觀看已截去上下肢的這一座「明城牆」!彷彿「它」是一個考古學上所稱謂的「遺物」、「遺跡」,表示「它」不是一個民國及共和國的所有,這在「它」與週遭環列並立的聳立高樓大廈,正可以展示出來「它」的「遺跡」之「孤遺性」。是什麼學問、什麼意識構成了我們的觀看這座「孤島」標名為「明」,--注定了要座落為一個「遺民」的「容顏」姿態。但事實上「它」又的確生存在民國與共和國時代--一直到我來此時,「它」都還是,只是「它」又老了些,「共和國」的「西安」人士正為「它」修補彩新粧,一直到我寫這篇「容顏敘事」時,「它」又更老了些!被稱之為「明城牆」的「它」,顯然在時間中顯出了雙重的性格,一方面「明」已經不在了,已是「歷史的」稱謂;一方面「城牆」又仍然存在,確實在現在還「活著」的那種活著,並且經歷風霜與歲月,高齡的紀年,曾經以居高之姿看盡 "幾度夕陽紅",然後漸漸年華老去,成為褪色的奇怪容顏,既沒有鋼、也沒有鐵,舊的斑斑肌膚只能證明黑色是它的容貌,木與樑是它的本質,昔日的高大現已老舊的垂首低姿。如果只是「城牆」,那麼歲月流入它的體內尚嫌不夠,不夠讓黑色染上肌膚。只有「明城牆」,當我走來觀看與面對,它的座落之姿態與容顏,才向我示:--低低訴說--「明城牆」是一個「遺民」!
這城牆是一個「明遺民」! 城牆上頭的一個角落,我「看」到了一個深痕,明顯是一把刀的劃下,必定是一段故事,一個敘事,或許是一場戰爭中一位士兵的抵抗,在死前的一把刀--不知是胡刀抑或漢劍的對決之後劃下,也許是一位守城將軍的長嘆之後的無奈,一劍劃下的戡入,已是這痕如此之深。 「刀痕」又成了「歷史容顏」向我「示」來。這裡,我必須要參照並且聯繫巴特的觀看「母親少女時的照片容顏」,來作這「示」中相同的疑惑,--我怎能在「照片之中」看到--並且還與其面對面--我母親在我出生之前的少女模樣在照片之中?這是怎麼回事?「照片之容顏」究竟向我「示」了什麼?因此,我又怎能看到千年以前的「荊軻刺秦王」與「霸王別虞姬」,2即便我已來至江邊的遺跡之所與聆聽著梅蘭芳!我怎能看到百年以前的故事 / 行動--「一刀劃下」?我能看到,我確實看到--眼睜睜地確實在此時此際「一刀劃下了的刀入石的交會」--其「痕」入我目來,在我眼前,與我相對。在我出生之前便已存在的「痕」,這是怎麼回事?一如我怎能看到千年前武帝於殿上怒斥了司馬遷的面容?「痕」是「證明」(巴特說的,照片特有的便是它的證明能力),還是「示」?如果「照片之中的十七歲少女」因為「照片」而依然揭示了「前者」的存在年紀確實比我老,是比我老的「痕」;那麼,比我老且我看不見、我不在場的「一刀劃下」,就是比我老、一直比我老、現在還高齡地與我面對、相視、相向的那一將我召喚至其「容顏」中的「痕」。
這是結論了:
「痕」是與我相對的「見在 / 整體」,還是百年、千年的「過去 /
殘片」--有個場域被稱作語境在支撐著這個片斷的語言?
三、作為祭文的一篇文本---閱讀際文中的哀戚
韓愈與十二郎韓老成皆少孤,韓氏宗族亦只有兩人傳宗,故愈與十二郎自少即有非常之親、非常之情,此愈之「祭十二郎」之「祭」所以深摯而悲,〈祭十二郎文〉之「祭文」所以悽婉而淒也。「祭」已往矣,「祭文」猶在。「祭文中的現在」充滿著追憶的筆調,召喚著十二郎「已是生前」的「過去」,置入「祭文中的現在」,成為「祭文」。試著找尋已無覓處的十二郎之墓,墓前似乎有個韓愈的容顏,正在臨墳而祭,傷泣的「容顏」在「祭文」之焚燼煙杳中依稀升起。然而,也無墓前、也無容顏,只有「祭文」的「敘事」。說 / 寫出愈與十二郎由生到死的「祭文敘事」。 我們「現在」已聽不見現場的臨弔之誦,也無可而視見現場韓愈悽淒焚文的容顏,更無法聽、見韓愈在「祭」的心態下俯案而書之下筆沙沙。又一個「現在」,我們,自被置放編入了的「韓昌黎集」中找到了文本---被稱之為有出處的「集、卷、葉」的 <祭十二郎文>之文本。開始「閱讀」到「文本」中的「敘事」,開始知道「文本敘事」中另一個「現在」的「追憶」,也開始知道那個「文」中的「現在」有「祭前」、「祭」與「祭後」。「祭前」已是韓愈的不在場,是已成往事的「憶」;「祭」是隱身於「祭文」中的當下性---或歷史性,心靈自第一字至於最末一字似真還幻地泊泊流向;「祭後」則是韓愈自墓前的返身,也是我們前去與「祭文」相遇之際。在與「祭文」相遇之前,「祭文」---有著「祭前」、「祭」、「祭後」之「敘事」的「祭文」,在與我們相遇之前,沒有「容顏」。相遇之前,我們亦正他處流浪。有「祭」有「文」的「祭文」,「文」猶在此,---種種的身世、飄零、流浪、安頓、圈點與標點,千年之後「在此」,在我手邊、目前,與我遭遇、與我相逢,我看到了「它」的「容顏」,是標點的「敘事」。「祭」的「容顏」,安在?一如「祭文」中「未死時的過往」,「在祭文中」其容顏也只能是「憶」的往事---韓愈用的正是這個詞。過往被追憶召回,握在手中,由寸管鋒毫注下,「書寫」了「祭文」,安住在「祭十二郎」的「敘事」中。流浪開始,流傳也開始,容顏又復不在矣!一直到「文本」出現,「敘事」中「容顏」才又充滿著感傷,呼喚著喚不回的「昔日」之「容顏所示」。不知是「歲月」、還是「衰老」,正慨歎著「生是向死的逼近」、或著「生命是聚少離多的永別」之體會。「容顏」,成了「文」中最深的刻劃之「紋」。
有標點的<祭十二郎文>書云: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3
有標點的「祭文」,文中有文,此即「去年」之「吾與汝書」。「現在的祭文」與「存在於祭文中的『去年之書』」同時存於我們閱讀的「祭文」中朗現。文中之「文」所「示」,是「去年」的「容顏之衰」,存於「祭文」的「敘事」的「與汝書」中,所述便是如上所云云之嗚呼者之嘆。「去年」如此,「今年」--對我們而言,豈是「今年」哉--又是何如?「容顏」正在「過去」與「現在」、「去年」與「今年」的字裡行間之「距離」相映中,更為「老去」: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我們閱讀到的「今年」,已經是「我們的過去」,崁入在文本中的「今年」入目。「去年」之「容顏」,「今年」僅在「文」中之「第十一行」可閱,夫可閱者亦已不復可見矣!可見者唯存追憶中,轉成為「文」中所書所引之「與汝書」之「文本」。「去年」之「文」,已在「今年」之「憶」,而「今年之憶」,又復成為「祭文」本身所透露出的「案前之憶」。「記憶」愈深,哀慟還深;在「記憶」中,往事成為深深的「現在」。「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由「過去」而來的「現在」,愈來愈悲痛,可悲者正在於「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海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魄不與吾夢相接。」可相守者,唯有一「生」與一「死」,以「夢」相接,「夢」逝,「容顏」亦衰,「衰而哀死」與「衰而哀生」!不僅此也,生命容顏之「朽」,尚出現在「他者」之容顏,「容顏」所「示」,凝於「我」之「視域」內:高堂明鏡悲白髮。我與他者皆有容顏所「示」之生命敘事。當你(妳)、我、他者攬鏡或行經古塘之水,映出的正是容顏之朽、歲月之痕。這些「映」出之「現象」:髮蒼蒼、視茫茫、皺紋,本身即是一種「書寫」,書寫于容顏,展現生命變化生成的刻記,亦是生存者自身擁有的「刻記」。這些「書寫/刻記」,當下正以「示」的姿態而座落,以座落之姿態而「示」,召喚面對者之眼神注目,容顏座落的姿態,不是一頁頁的「情節」與「翻閱」。只以「蒼蒼」而「示」,書寫于「髮」上;以「紋皺」而「示」,書寫于「顏容」之上;以「容顏座落」而「示」,待有人來「容顏敘事」。 容顏「示」了什麼?「蘊」了什麼「敘事」?此一問題對你(妳)、我、他者自身之生命皆有意義,問的正是自身之容顏,及其所「示」於「顏容」上之「書寫」,正是此一書寫,可以展開---透過「再書寫」,對「書寫」的「再書寫」---為「容顏敘事」,由是我們必須正視其「示」,凝視關注且有領會,從而將此「領會」---對「容顏/髮蒼蒼/刻記/書寫」之「示」的領會「書寫」下來。對此「書寫 / 示」的「再書寫 / 語言文字」,遂成了文本,這便是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文本。 一篇「文本」的身世,緣於歲月之痕對身體的書寫,在現象上有了「髮蒼蒼、視茫茫」,此即是「生命」之「示」,「身體」之自我刻記,見證著生命正生存著。我們必須對此有所領會,從而將此領會---對身體書寫與刻記所「示」的領會書寫下來。對「書寫」的「再書寫」,以語言文字進行的「再書寫」,於是便形成了「文本」。「在文本中」,生命「示」其所「示」、「在文本中」遂有「容顏敘事」---一種詩之性格與語言狀態的「文本」。 由是,「容顏」乃成一「示」的姿態,生命在其中顯其奧義---生存者持存之開顯與凝聚,朽與生成即蘊於其中。「書寫」其「書寫/刻記」,將之成為一個「文本」的事件,就是對「容顏所示」(有當下性的瞬間所是)的「敘事」(以歷史性為基的力圖追摹)。「去年」的<與十二郎書>與「今年」的<祭十二郎文>;「當時」的「容顏所示」與「現在」的「敘事文本」對「過去」的追摹與記憶,以及身在咖啡館中的我之書寫,如果你 / 妳現在當面的姿態是「閱讀者」的話!
1 這裡指的是羅蘭巴特的《明室-攝影縱橫談》(大陸本,趙克非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1),以下同。
2 這問題置於歷史學領域中,便是:「"歷史"是如何可能的?文本,閱史?照片,存真?古迹,考古?」1 這裡指的是羅蘭巴特的《明室-攝影縱橫談》(大陸本,趙克非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1),以下同。
3 韓愈,《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6),,卷23,祭文二,頁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