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經典的聲音
--有關《傳習錄》的「閱讀」
李 紀 祥
一、《傳習錄》:文本的傳世形態
從王陽明生前到他逝世之後,陸續由王陽明的弟子們編纂而成的《傳習錄》,迄今已通行於世間四百多年之久,從某方面來說,這本書已經被許多人認為它是一部中國人所必讀的經典。錢穆先生曾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六祖壇經》《老子》《莊子》《近思錄》《傳習錄》列為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典,其中《近思錄》、《傳習錄》兩部書籍被選入,反映的是宋明新儒學(Sung-Ming Neo-Confucianism)在中國文化與思想領域的地位。《近思錄》由朱子與呂祖謙編纂,凝結了北宋時期四位思想家的文本與語錄;而《傳習錄》則由王陽明弟子所編纂,初刻本在陽明生前即已刊刻,編纂與刊刻的目的都是為了傳播王陽明的思想。
現在我們看到的《傳習錄》版本,也就是一般通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可以稱之為「定本」,這是在王陽明過世後才完成其演歷的版本,從王氏生前到其死後,初刻的本子從一卷本而逐漸向三卷本演變,參與的弟子包括了王陽明弟子徐愛、薛侃、陸澄、南大吉、錢德洪等人;從最早的抄本到初刻本、續刻本、合刻本、重編本,從一卷本到兩卷本、三卷本,《傳習錄》三卷本的成型,學者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定論,比較可能的年代是在明代嘉靖35年或是37年;當時王陽明已經過世。
在《傳習錄》的三卷中,其實有兩卷嚴格說不能算是「寫作」,而只能稱之為「紀錄」---一如《論語》那樣;雖然其經過流傳之後,已經以「文」的形態向我們傳遞訊息,這點迫使我們必須以「閱讀」的方式來對此書進行訊息的重組,從這點來說,《傳習錄》作為經典,與其他經由「作者寫作」而來的經典,在表象上並沒有甚麼不同;但實際上,經過「閱讀」的中介,「閱讀者」還必須進入本書那原初的場景:師生之間的對話場景,才算是真正的進入了「記錄性經典」所想要保存的世界;這也就是說,在「閱讀」之後,「閱讀者」還須要「聆聽」,才能「聽見」王門師弟對話的聲音。因此,這使得「閱讀」《傳習錄》有了一個極為特別的進路:這便是閱讀其聲音的傳達。如此,閱讀便不再是一般措詞意義上的視覺閱讀而已,而更是一種聆聽。
筆者認為,從《傳習錄》最早的版本---抄本形態來看,這本書從一問世就已經決定了它的性格:顯然是「紀錄」性格的,也就是以「文」來追記「言」的。一方面它要記錄的是當下的老師與學生之對話發聲的場景,沒有聲音就無所謂「記錄」;另一方面,最初的版本之所以是「抄本」,那是因為最初以《傳習錄》來命名書名的本子,就是從徐愛所記錄的本子而來的;徐愛既然將他從老師王陽明那裏所接受的「聲音」留下了「文」的「記錄」,而這樣的「記錄」又在王陽明生前就被稱之為《傳習錄》而傳抄於同門之中,這已經表示「傳抄」以及「抄本」作為王門經典的歷史已然在王陽明生前便已經出現了初步的「文本」---抄本型的;則這最初的一卷本《傳習錄》,意謂了《傳習錄》的問世與誕生,是「以文記言」的「記錄聲音」類型的,也意謂著比徐愛的「記言之文」還要早、還要根基的時空,便是:「聆聽對話的聲音」。換言之,「對話」發生在「紀錄」之前,「聲音」是此一經典的根基,而不是「文字」;但「文字」卻是《傳習錄》作為經典並且流傳的樣態。《傳習錄》是一本須要「閱讀」的「文字性」經典,既非「錄像文本」、也非「錄音文本」。
二、三卷本中的兩卷與一卷
三卷本的《傳習錄》,「卷上」與「卷下」都是屬於「紀錄」的性質,紀錄了王陽明與弟子們之間的論學對話,這裏面可以讓人產生聲音迴響於人物發言場景的想像。而「卷中」的部份,則是從王陽明與同時的學者、學生的親筆書信中取材,改編成為對話的體裁而彷彿「遠距離通信者」就是「近距離對話者」。
對於「卷中」而言,雖然王陽明的弟子,從南大吉到錢德洪,都把這些「書信」編成了「對話」的體裁,但實際上,「卷中」仍然是屬於標準意義上的書寫與閱讀,只是加上了對話的戲劇化效果,彷彿「編寫劇本」那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傳習錄》的編者想要加入一些由王陽明「親筆書寫」的資料作為此一經典文本的成份。將《傳習錄》由弟子的「編輯」改換裝扮,換裝成為可以冠上「王陽明」之名的作品,以便在當時宣揚王陽明對抗朱熹的思想,應當便是這一換裝舉動的真正目的。但是,一方面是加入王陽明親筆的文本之換裝,一方面卻又是為了配合原來的體例---這意謂了即使《王陽明全書》已經刊行,但是《傳習錄》的影響力還在,因此,有必要保留這一書的原來形式:也就是以「對話」為主的「記言」形態,於是,遂有將王陽明的親筆書信改編成了「對話體裁」的「改編舉措」。這樣的法其實有些奇特與奇怪,迄今尚未有學者提出質問:為何會如此?既要冠上王陽名之名的親筆「寫作」作品,又要「改編」此一作品成為「對話劇本」;那麼,究竟《傳習錄》的作品定位,是應當朝向「原初場景」的「言」作定位呢?還是要朝向以流傳為主的「文」作定位呢?我自己認為,這一問題實在不好回答,也是我自己給自己提出的一個「我的難題」!我個人認為,《傳習錄》的定位應當是「記言」的:換言之,它既是「言」的、也是「文」的;就「文」這一部分而言,我們應當由「閱讀」進入它的世界,就如同讀一部劇本或是歷史、小說中的對話情節一樣;就「言」這部分而言,我們則應當學會「聆聽」,學會傾聽經典中文字發出的「聲音」,宛如王陽明的親身再現,在與弟子們面對面的對話現場中,吐出教誨與指點的聲音。
參與過《傳習錄》編纂的王陽明學生南大吉在〈傳習錄序〉中曾提到了《錄》與「錄」的意義:
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天下者也。
第一個「錄」字顯然是指「書」而言,因此標點符號上應當作:《錄》;第二個「錄」字,則指得是一種動作,尤其是對現場式的「言」所作的「文」的「記錄」的動作。沒有「記錄」的動作,將「對話」或是「聲音」記錄下來轉換成為「文字」,也就不可能有「刻」的文本傳世與流傳!
三、由閱讀進入聆聽的經典
筆者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近思」之《錄》與「傳習」之《錄》〉,詳細討論了這兩部代表宋明理學的經典,尤其是兩部書的書名中各有一個看來相同的 “Lu(錄)”字,而看起來是相同的符號,意義指涉卻大不相同。近思錄是由朱子所編纂的北宋四位理學大儒的著作選編,因此朱子是一位親自參與的編者;但《傳習錄》卻是由王陽明的學生們陸續編纂而成,由王陽明學生作為編者的書卻歸到了王陽明的名下,彷彿王陽明便是一位作者。我們對於這兩部書的印象常常是與朱熹、王陽明聯繫在一起的原因便是來自於這樣的一種背景。因此,這兩部書的書名中的”Lu(錄)”字看起來雖然相同,但是意義的指涉卻是大不相同:一種是屬於閱讀的,閱讀朱子所選編的文字,來追求閱讀者的自得於內心;一種則是傾聽的,閱讀王陽明與其學生們的對話,從文字中去傾聽對話的發言聲音,也是要聆聽者得到內心的自得與感受。有意義的是:者兩部經典中的”Lu(錄)”字便剛好在書名的書寫與刊印流傳中見證了字己的存在屬性,也見證了宋明理學(Sung Ming Neo-Confucianism)中所顯示出的兩種教育類型。
筆者在求學時代,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某一個晚上,明月當空而皎潔,筆者忽然感受到歷史像一條長河,而古人們的聲音便透過這條長河而傳來,筆者當下能親切地感受到為我所閱讀的文字之中的先賢的聲音。我們都知道,夜晚我們所看到的銀河之中的每一顆星星之光,雖說是現在的光,但實際上卻是幾千萬光年以前的存在、也可以說它是由已經成為歷史的星星所傳來的光;如果我們能看到已經是過去的星星之光於現在,那麼,從傳世的文本之中,我們也能聆聽到古人被文字所轉錄下來的聲音!
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聆聽經典的聲音
於
下午3:25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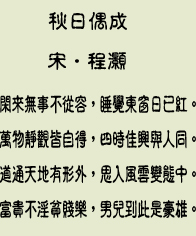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