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世界的文化版圖與視野
近代第三華人世界論述
李 紀 祥
提 要
自魏源《海國圖志》以「海」言「國家」、由「洋」觀「世界」以來,「歐洲諸國」於是一變而以「西洋」稱之。魏源實乃一變古之道也,正與漢、唐時代之以「陸域」視西方諸國而稱「西域」相對。
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迄於今,已逾百多年矣,昔年所割賠地今皆已收回,於是形勢又當一時代之臨與夫氣運之際。古有漢武、唐宗,衰匈奴、竭突厥;今日則中原華夏,陸路亦通,以西法而可以籌鐵路,穿絲路、越中亞而直達魏源《海國圖志》中由「洋」所識之歐羅巴洲諸國;則所謂「西方」諸國者,竟由「洋域」以通之耶?抑復三代漢唐志古之道而由「陸域」以通之耶?時魏源氏所謂「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者,方稱之為「新議」;若是,則一百六十年來,或曰自滿州入關以來,又或者竟曰自明季利瑪竇入華交通以來,已四百多年矣,時正當孟子所云文統繼運之世,則由「西洋人譚西洋」以求「洋域」之視野者,齊一變而至於魯也;有志於三代與夫漢世唐世,魯一變而至於道也。志周、孔之道,繼孟子王道之言,其要點在華人文化版圖觀之視域如何可論,曷霸權之有。
一、三個華人世界提出之緣起
筆者在本文中,嘗試著將近代以來華人世界的文化版圖,作一分野。在筆者的視域中,望見的乃是一幅落實於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文化版圖。標題所謂「三個華人世界」,乃是本文所以立足的重要觀點,由此而望見的的華人世界,不論是歐美華人所命稱而相對於其「國籍」的華裔,亦或是從中原而源出的「中國人」之命稱,還是海外具有長遠歷史的閩客海上移民之唐人 / 華人的命稱;都可以出現在筆者此處所謂華人世界的版圖視野中。
所謂第一華人世界,乃是指源起於中原的諸華夏民族與歷經歷史不斷南移播遷的華人,包括現當代已經存於台灣而出現統一與分離運動論述的華人,皆在此一第一華人世界的文化版圖之內。在台灣的閩客族群與南洋閩客華人之不同處,乃在於經歷近代的國共分別建立國家之後,在台的閩客華人,深深與四九年播遷的國民政府交相纏結於一個自我身份認同之中,而以國家型論述而自稱為「台灣人」;而南洋華人則在民族國家之建立下隸屬於馬來亞、新加坡、泰國、印尼等近代國家,也有其在地化與回歸中原故鄉與否的方向之爭。因此之故,台灣的華人因為國共之纏結的歷史原因,共產政府遂於民族與血緣論述上,跨過一海---台灣海峽---之隔,將台灣視為一個對內尚未結束的內戰,卻又不願再發生內戰,而欲於民族論述上成立並完成一個以大陸視野為視界的「中國」,在這個論述的視界中,其邊界乃是大陸形態的,向東及南,均止於沿海之大陸的海岸線;於是,遂將歐美以及南洋乃至世界各地的華人視之為「海外華人」。換言之,此一大陸型的論述中,海外華人乃是隸屬於別的國家之國籍中,出入中國,以及在中國「境內」移動,皆須一本國籍之護照。這點類型上的特色,察之於台灣的華人之國家形態,亦然。兩岸在此果然是近代史上分由國共北伐之後所主導的華人世界之類型。也是因為如此,台灣始終無法脫離近代式的歷史形成,也一直無法形成真正的海洋觀點,也不類於其閩客祖先們的海上移民性。更是對於自身歷經葡、西、荷、日之歷史,猶在浮沉,以是只能以1949年來作為自身騷動不安的歷史意識與國族建構。這樣的建構自身,也使得台灣欲就自身所在之「土地」---這其實是大陸型觀點,而不是海洋觀點---來意識並自覺自身是「台灣人」。台灣因為採用的歷史定位自身的乃是「近代史式」的模式,從而常常忘卻了從歷史長河中祖先的足履來環顧四周。於是,筆者在馬來亞檳城的一家向海的飯店中,竟然沒有反應過來,也沒有意識到:當飯店中一個打掃清潔的老婦人對筆者善意的詢問是否會說「福建話」時,筆者以為它與「台灣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所以一下子意會不過來,而愣在那兒,一直到老太太說「你方才說得就是福建話啊」!這才意識到兩岸所共同建構出的「台灣同胞 / 台灣人」,所說的「台灣話」,原來對南洋華人而言,只是1949年以前「海峽兩岸」尚未形成就已存在的「福建話」。我們的視野是多麼局限於台灣所形成的氛圍之中。
對中國大陸而言,「福建話」是福建人的語言,「台灣話」則是是台灣同胞的語言,雖則它們都有所謂的「南方口音」。然而,對南洋華人而言,他們說的語言就是指來自母體華人世界南方的福建話。那麼,「台語」究竟是福建話,還是河洛話?這就牽涉到不同的歷史階段之歷史記憶的選取,以形成聯繫現在的自我。從「源」而「流」、從「過去」而「現在」,「歷史」所供與的乃是自身所在之文化世界的認知資源!
而所謂第二華人世界,乃是以香港、澳門作為指標。「港、澳」在1997年回歸「中國」的意義,乃在於其近代性以及西方性,這是由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肇端下在中國之「境內」所不斷形成的「西方 / 近代世界」,縱然領事裁判權等已經消失,然而,由洋房、領事館與銀行所形成的建築景觀,仍然成為了1997年之後的「現在遺跡」,並融入城市中成為近代中早期的西化風格之景觀。反之,若1997年是對南京條約以來不平等條約的最後一筆抹去,則中國於1997年對於「港澳」收回的定位,已經反指涉了「中國」概念建立的近代屬性,乃是自帝國主義殖民中解放的意識,並以此為歷史主軸而建構了自我屬性的國家定位的概念,以及其「建國之近代史」,這種「近代歷史世界」的上限與起源通常來說就是鴉片戰爭。「近代史」所構成的「歷史世界」及其起源認知,所形成的正是自我認知與定位的涉入。「近代史」也一刀將中國傳統性的「朝代式認知」而將「清代」斬成兩段。從此,研究「清史」與研究「近代史」是全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儘管兩種範疇在道光以後是重疊的,但是,近代史的研究毋寧更為注重如何至於現在形態與現在世界之樣態的起源性歷史之因果研究論述與解釋。從「港澳」切入,則不論是五口通商之五口,乃至於我們現在在上海外灘、武漢江灘、天津、青島、威海衛所見到的異國風景,都是類同於「港澳」的異國屬性,並在近代世界中被加之以殖民的歷史論述。在這些異國持有地的華人,筆者將之稱為第二華人世界。第二華人世界在現實中彷彿已經消失,結束於1997年的回歸。然而,港澳---特別是香港華人其意識中對其自身源自於英吉利政治意識的認知與習慣,正是1997年之後歷史的繼續遺留,這種意識的根源實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之認知有關,而更可上溯自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對於西方及其殖民地的比較認知之目睹中。
第三個華人世界,則筆者主要指的乃是作為母體之外的華人世界,通常經由母體華人世界的向外指稱,慣性上稱之為海外華人。大體可以別為兩類:一類主指在歐美的華人。歐美華人所構成的自我認知,仍是近代性意義上的,以是這一類華人在深層意識中多有西化之傾向。或者說,他們在語言及構成語言的文化、國別之語言性上,必須西化。另一類則反之,筆者主要指的是在南洋地區的華人世界。南洋華人的特別意義,在於其存在以及我們對遺存在的歷史認知,足以顛覆所有以「鴉片戰爭」作為「上限」所形成的「近代」之「中國」的概念,也迫使第一華人世界以近代性來構築自身歷史以及國家之邊界視域的必須反思與重構,否則即無以面對世界中的華人以及華人世界。南洋華人世界乃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已經形成。
二、新世界華人觀之重省與鴉片戰爭作為近代上限之歷史解構
作為第一人稱同時出生成長在台灣,也是在台灣形構出華人世界其其文化與近代變遷的筆者,在第一次來到南洋華人世界時,立即面臨了的,即是其認知系統中的解釋南洋華人文化現象的不足,這種不足,暴露出的正是生成於第一華人世界於疆界思維上的陷入困境與窘迫。尤其是本科專業為歷史學的筆者,正是因為明白清楚地從歷史文本上知道這些華人乃是自元、明、清以來即陸續自第一華人世界之南方而向外遷移,早先並無所謂「西化東來」所造成的「歐美華裔」之華人世界構成的特性。同時,南洋華人世界在經歷近代西方文化之東南來之後的「西化」與「近代化」現象也有其特殊性,未必與第一、第二華人世界的歷史觀與世界觀相同。於是,在三個華人世界自身所提供的對於華人世界之母體文化性之解釋能力上,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之動向上,何者具有較大的優先提供性,就不是母體與海外與否所能獨佔的了。尤其是在一個世界華人對於華人世界的空間 / 文化版圖與時間 / 歷史之縱向性格上,由共黨與國黨所形構的政府解釋之官方歷史版本,是否能反映更真實更深刻的「華人版圖」與「華人歷史」,還是一個可以提出的質問?這樣,無論是處於更為西化的歐美華人,或是另一條自明清以來經歷著不同的歷史發展的南洋華人,他們對自身歷史與現在定位(自我辨別與認同)的觀點,有可能較諸於只具百年上限的母體之近代性形構觀更為深入悠遠的歷史長河當中而迄於現在。
這個南洋的海外華人世界,早就存在那兒,「早於」近代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的概念形成之前就已經在那兒。然後才與中國大陸的清廷、晚清、民初北洋,以及國民黨的國府、共產黨的人民共和國,各個歷史階段所形成之政體,分別在不同的地域,一起遭遇西化與近代化。這一作為母體分支的不同遭遇,卻也是足以沖擊作為母體的第一華人世界予不同的歷史方向也是不同的歷史中國之概念下的歷史遭遇。就筆者而言,早在寫這篇文章宣布調整了的三個華人世界概念之前,就已經通過「旅遊及觀光」接觸過這個世界,但是,也仍僅止於「東南亞」。「東南亞華人」的讀法就是大寫的「東南亞華人」,彼時筆者尚未意識到此種讀法中崁入了多少近代史的上限的「圍城」之框,無法認知到五百年前儘管不是一家,但是五百年後卻因為「南遷」而在南方的陸地與海洋享有不同卻又共同的「北方」。許多人,相信包括一百多年歷史的海峽兩岸的人,更多的是成長於歐美的華人,所懷有的皆是西方觀點下的「東南亞」---而不是真正地理方位上的「南洋」,一如中國、日本、韓國之隸屬於的是西方版圖眼界下的「東亞」。而從台灣去「東南亞」旅遊,就是東南亞的概念,東南亞對筆者而言,就是許多國家的構成,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等。沒有甚麼不對勁,「中國」這個國家,是由兩個中國在中國內部相爭誰為一個中國的正統的那個「中國」,內戰的分界線由古來的長江南移到了台灣海峽。這種認知上的理所當然,一直到檳城的世界初次出現在筆者的有所感與世界之中,筆者才赫然發現,一個成長於台灣的華人,為了尋求華人文化之母體,幻想於神州之想像,於是,大陸成了調整在台灣成長的歷史文化的座標、參照與歸屬,「海峽兩岸」成了中國世界的全景圖。台灣的自我認知,隨著一海之隔,形成了分裂時代的正統論述,宛若魏晉時期的長江之作為「一統論述」的南北界限。隨著這一海之隔,不論是統還是獨的論述,都是依著這一條「海峽」所形成的「長江」而自我建構著。「統」所不能割的乃是國共共同建立的近代之中國國家;而分離所幻想的仍是近代以來模彷西方進步意識的以舊中國為恥的新國家想像,在中國尚是落後時,將殖民、被統治、經濟與政體一齊包裝為一種新的望見之想像,忽略了的乃是文化與歷史之深層,於是,自我乃陷入歷史的空靈與虛懸之中。此種格局的思維之最大特色,就是不能從歷史與文化的察照中,回歸宗法與祖先意識的文化之源與流來看待自我的過去與現在。台灣的一切反中國論述,不只是被視為只是「台灣的」,其語言、人種、族群,也出現了台灣語、台灣人的構圖與措詞,忘卻了乃是在它的「近代史」之前也還有「史」,且與南洋是同一來源。而南洋華人世界的意義,便在於此地華人文化世界的存在,使得一個來自台灣,成長於台灣,並且心懷中國想像的外省人---也是一個學習歷史的人,遭遇了另一個中國,既非台灣視域,也非投向於大陸的中國視域;檳城飯店中的一愣,便是一個真實的瞬間,由原本以為、不解、錯愕、意會,這一短暫的個人經歷,放大了來看,不正像是中國之近代以迄現在的縮影;一個真實存在的在台之華人的個人之經歷,放大其時間度數於百倍千倍,就像是知識份子對中國百年之近代史觀看之眼界,這種看待歷史與文化版圖的專業眼界,有沒有問題可以提出而深省之呢!南洋華界的意義,使得筆者發現了:自己只是從台灣的局限中想像文化情懷,即使意識到自己能反省,但也僅只於大陸,從黃河、長江而迄於海峽,或者由海峽、長江而迄於黃河、中原與昆崙,從而匯合海峽的兩岸而成就一己的母體文化之想像。而這,由國共兩黨承擔起來的近代中國,以及其所論述出的中國歷史的家園,就真能是中國的一切嗎?---包括文化版圖與中國想像!南洋使我們遭遇了太多的例外,也暴露出一個長成於台灣的華人,其歷史觀及文化版圖視野的局限,更照映出大陸母體文化的現代化表相之有餘,而對歷史文化長河中的自我認識之不足。不止台灣的「統獨」場域不能提供范仲淹型知識分子的文化情懷:有著居廟堂之上與處江湖之遠的位所;而前瞻中國未來的視界,也必須從歷史中體會出一種身所在的深遠與深刻才能承擔得起前瞻。
三、第三華人世界的文化版圖意義
---文化母體的版圖視域之必須重省
(一) 海洋視域不能祇是五四式與河殤型的
中國有沒有海洋觀點?觀乎近代華文歷史課本於中國近代史那一系列章節所陳述的,必然是沒有。魏源的《海國圖志》便可以堪稱是這一種新世界觀的代表著作,其書名中以「海國」為世界版圖觀的呈現用詞,就是「洋」的觀點。同時魏源更在其書中明確地說道:「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1]如果我們的問題由魏源來回答,其回答便是:「沒有」。在這樣的「西」之「洋」觀透過教科書之傳播與教育下,百年來我們的認知其實都認為,自航海性之地理大發現以來,海洋與資本主義都是西方的。隨著西方人的東來以及扣關,中國這一古老的大陸國家,才逐漸由海口與港口及租界打開了自身,慢慢接觸了西方的海洋世界及其所帶來的海洋文化,東與西的遭遇,就是一部不平衡的中國近代史,就是大陸型文化的中國與海洋型文化的西方接觸的歷史,也是起源自愛琴海的藍色文明與起源自黃河中原華夏的黃土文明的遭遇史。大陸於文革後再度談改革開放的主調就是「河殤」這一部中央電台播所播放出的主調,同時也是兩岸中國人教科書中傳播教育的歷史主調。一部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中佈滿了章節內容與標題的,無非就是「鴉片戰爭」之屈辱、「自強運動」之向西方學習洋槍大炮、「維新變法」的從學校、制度入手之制度面的向西方求法、「中日甲午戰爭」之徹底失敗而使「革命」成為主流從而也從「革命」畫分了新、舊意識的標準---「西化」與否,五四的西化或新文化運動正是一種以西方為師的思想辨識運動,辨識的是不僅是學習的西方,也是自身的一次全盤重省。這個西方,不是傳統上的西戎之羌、也不是波斯阿拉伯、亦非西域,而是「泰西」、是「西洋」,是以海洋文明作為主體來認知的西方。「河殤」中便是用藍色來代表西方文明,也就是海洋文明,一部「河殤」影片,播來便是一部藍色樂章。「河殤」中的藍色,寓意的是古老守舊保守的長城,必須要開放,而落後的黃河,流了千年,終須望向大海而進入世界,向著藍色的大海才是一個滔滔不能停歇的歷史流向於未來的方向。這是執舵者的宣言。從清末以來孫中山迄五四新文化運動乃至於共產黨的治國意識,皆是如此。「河殤」中從近代中西文化的遭遇中所認知的正是中國沒有海洋觀點。中國的「沒有」以及中國的「有」,於焉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向藍色文明尋求海洋出路的「能有藍色」的歷史行程。既然這樣將自身母體世界定位成大陸型態於近代,其焉能不將自身國家的邊界只放在海洋之內的海岸線,以便製作出一個向藍色學習的版圖及視界,又焉能不將在海洋世界中的華人世界稱呼並視之為海外華人?
(二) 南洋華人世界所提供的海洋觀點
80年代,為了突破政治政體分裂上的困境,提出了「文化中國」的概念於復刊的台灣版《文星》雜誌上,這是已故的哲學家兼美國漢學家傅偉勳先生所提出的。後來這個「文化中國」的概念頗為美國的華裔漢學家們所接受,將之移動到了東南亞的華人世界之論述當中。在杜維明的一篇〈「文化中國」初探〉[2]的文章中,便顯示出了這種「文化中國」的概念由海峽兩岸的第一華人世界向其它地區華人世界之移動。這其實還是與新加坡有關,新加坡的李光耀在「資本主義與儒教倫理」的聯繫影響下,企圖建構一套不同於西方的倫理內涵的論述,因而由杜先生來規劃。這是一個現實的背景,筆者且不去談它。值得注意的是杜先生在一系列文化中國論述中,已經展開了他的華人視野,他將「文化中國」中有關「華人 / 文世界」從概念上區分為三個世界以便能描述歷史與當時的現況:其一,由在大陸、台灣、港澳及新家坡以華人為主的社團所形成的第一意義的世界。其二,全球各地中以少數民族自處的華人社團,包括人口數達百分之三、四十的馬來西亞華裔,及不及百分之一的美利堅華裔和比率更低的拉美、中東及非洲各國之華裔所組成的第二意義世界。其三,由散佈全球不分種族、語言或職業直接參與研究、學習、介紹及傳播中國文化的知識人士所建成的第三意義世界。
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他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人世界分為兩個不同的世界了。為什麼新加坡屬於與母體中原之大陸世界為同一個世界呢?也許是因為杜先生本身雖然源出於台灣,但在自我身份立足上實是隸屬於第三華人世界中也即海外世界的美國漢學家,所以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接觸較為密切,因此,在認知上便由這裏出發---這自然是因為新加坡國大的學術世界是近代式也是西化式的。因而杜先生便完全不能理解馬來西亞華人在國家教育體制外力撐也是苦撐獨立中、小學辦學的意義,也完全不能理解更是未嘗體會到一個歷史長河的背景認知之分歧,在此分歧中,已足以將自我定位也暴露出自己的認知是基於西方視野中望向東南亞的,因而他只能從國大看到新加坡的極度近代性(西化中對儒學的提倡?),而不能從1957年馬來亞成為回教獨立國家之前與之後的獨中與獨小的華文辦學中看到馬來華人世界的百年以上的長河歷史之深遠性。我想,杜先生和沈慕羽先生的差異,差不多就在這裏了。沈慕羽先生在馬來西亞華社中甚為知名,但在海峽兩岸以及西方的漢學界與華人 / 文界中,卻知者甚尠。他曾獲得過台灣所頒的第一級「文化獎章」,這個獎章頒給「海外華人」尚屬首見;在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的一次「祭孔大典」上,他曾是特邀與祭的貴賓。他的一生如果放置在「近代華人史」中作定位的話,有兩項歷史定位,對沈慕羽來說,顯得特別突出---其在「馬華史」上參與「馬來西亞建國史」的事跡則不與焉,因為近代域內中國的「革命史話」之英雄實已多得不勝枚舉。其一便是筆者提到的有關馬來西亞在馬來語/文為國家教育體系中作為獨霸式的「國語/文」時代,他成為「華文獨中 / 小學」運動的歷史符徵;其次,則是他一生提倡尊孔,倡議孔教。因此,沈慕羽在中國的南方域外之提倡中國文化與尊孔,與杜維明在中國之域外西方的學術願景以及從儒學立場與西方宗教之積極對話的展開,其在精神上固頗有神似,然從歷史背景上望之卻又有大不同!迄今為止,筆者尚未聞治儒學、儒教、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者,對兩人作出過比較研究之探討的任何論、著,以及由此而提出過關於文化中國邊界概念與跨域的思考,尤其是從沈慕羽與杜維明的比較來作思考,思考一個域外中國概念上「古」(沈慕羽的華化代表著歷史背景座標中的「古」)與「今」(杜維明與西方歐美漢學與宗教學界的對話代表著歷史背景座標中的「今」)的可比較性的議題:「對話:域外華人世界的『東』與『西』」。
讓我們停止對沈慕羽的介紹而回到杜維明從新加坡出發的議題與概念上來。為什麼新、馬分屬於第一、第二的意義世界呢?新、馬為什麼被分別開了呢?杜先生顯然已經缺少了一種歷史的文化眼界,這完全是他不曾感應的的華人世界,甚至連東南亞---或稱南洋的華人世界之與歐美的華人世界之俱都屬於第三世界的海外華人世界,這點,杜先生也缺少感知與認知。如果我們對當年杜先生曾經接受過馬來西亞的官方邀請而至馬來西亞大學作過層次極高但卻獲至與新加坡完全不同甚至走樣的反應尚有記憶與認知的話!
自宋明以來,中國大陸沿海便逐漸地開拓了海上世界,包括海上移民與海上貿易,自然也包括小型戰爭---稱之為海盜,顯然是非常大陸觀點的。南宋時的海上貿易有南北兩方,北方以高麗及日本為主,大多是溫州以北的江浙人;南方則以閩客人為主,向南洋移動。中國的海上華人世界及其抵達於南洋的新天地之陸地的文化與僑居之移動也在迄今六百年來逐漸形成。在這海上世界與陸上世界皆有華人的歷史之局中,中國有沒有海洋觀點呢?我的看法是:有的。只是,中國向來以大陸形態為立國之形態,世界觀的外來者—異族係集中於長城與西北的歐亞大陸上,所以即便其視界中有海洋觀點,也向來被遮蓋在大陸型世界觀之下。大陸型的世界觀,下意識以成習的,乃是習於以沿海之陸地邊界為其視界中世界之邊界。但是明清六百年來海上華人世界的出沒,顯然已經使得---至少在南方而綿延向至南洋的海上移動,隨著船舶之海上移動,船隻所形成的向陸上之回眸,回眸視域中的大陸之邊界,已經不能再是一個大陸國家或母體的邊界了。船隻所至之處,與陸上出發之港口,兩點間所形成的直線與風、與浪所形成的曲線,「海」也是視域中的華人世界之構成,早在近代鴉片戰爭之前。
那麼,中國有沒有海洋觀點呢?我的答覆與我的看法已經很顯明了,有的,在南方的移動與移出及歸鄉之華人所構成的世界之中,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明代人張燮所著的《東西洋考》及清代初年陳倫炯所撰的《海國聞見錄》,則其書中的南方海洋世界觀顯然便是不同與居位北方的大陸型世界觀者的。只是這種南方喊洋世界觀常期被遮蓋在向來以大陸型視界及其以陸地沿海作為國家邊界化的視界之下。當近代中國這一國家建立之後,無論是四九年之前或之後,中國的海洋觀點皆來自於「河殤」所代表的向西方尋求之出路式思維與意識之主導,所以中國的邊界仍然不越沿海而以沿海為界,越出此一大陸之邊界,便是西方藍色式海洋思維之啟程。於是,南洋的華人世界,便在近代鴉片戰爭之為一道橫切線下一分為二,我們不能將其前的歷史納入我們所在母體的視域之世界之內,「東南亞」依舊是使用的稱呼;甚且在現今的大陸之各個大學中,「東南亞」這個世界只有出現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研究機構中,標明的是國與國的關係研究而不是歷史研究納入了華人世界的關懷,其差別就在近代的國家類型之「域外」與歷史長河而下的觀點所能提供的「域內」。這便是南洋華人世界所能自歷史長河中六百年來一點點一滴滴喚起母體記憶歷史的意義。同時,作為母體的海峽兩岸,且不論這個「一個中國」之棋盤中的兩個正統論述,原來在歷史中向來是發生在長江南北的楚河漢界,現在微妙的、也啟人深省的,向南推移到了台灣海峽的海洋性。這一道海峽,不僅在過去是一個與南洋共同記憶海洋觀點與南方華人世界的海峽,也是在四九年以來代表中國之內部的兩個世界的分界線:南與北之正統論述相爭且象徵大一統來臨之前的的分裂論述之分界線,已在歷史推移中由長江而向南移動至此。這個由長江而南移的象徵及其分界之屬海屬陸的意義及其歷史昭示,還能不猛啟長長之思與深深之省麼!
最後,我想對第三華人世界再度闡釋其分型及所以然的理由。在筆者的望見中,歷史中迄於現代所形成的華人世界可以分野為三個。其一是中國、台灣地區,屬於華人文化版圖中華人世界的母體;第二則是自南京條約以來,在中國母體境內所形成的租界,尤其以香港、澳門作為最近的歷史之於現在的發生事件意義,正可以考驗我們對於自身詮釋的深刻度如何。第三則屬於「海外的」華人世界,包括歐美地區與南洋---或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世界地域。而更可以隨著中國自身之接受「近代 / 近代化 / 近代史」此一詞彙及其概念,而將海外華人世界又區別為兩型:歐美華人在其所居地域之內是逐漸也必須西化,以追求自身的可存在及尊嚴地存在,屬於近代以後發生的事件類型,也正是近代的格局下華人世界的發生事件;然而南洋的華人卻是早在近代出現之前---也就是鴉片戰爭之前,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已出現於世界的文化版圖之中的發生事件。南洋華人世界不惟不以西化為其「身 / 生為華人」之自我認同,反而以拼命保存母體之華文化作為自我延續之意義,祖先與子孫是在文化意義上承與傳、源與流的。這樣,當海峽兩岸的母體世界將歐美華人世界視為海外華人時,反映的,正是自身的視界之在中國近代史式的近代化行程中;以致於不能將視界及於六百年前以來的海上視野中的南洋華人之「第三華人世界」的存在與生存之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出現的第三個華人世界,與前述通過與新加坡連線而建構三個文化中國意義的論述之差別所在,便是在於「第三華人世界」眼界的提出已經將華裔漢學家自身所在與南洋華人所在一齊歸為海外華人的第三世界,同時也將其作出區分;通過這樣的版圖視界之自省,及與此而相連而來的海洋觀點之能否有別於近代式的河殤藍調式之海洋文明觀;以及作為中國之國家的沿海之大陸邊界是否就真的是中國即將成形的文化版圖之邊界;本文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因之,大陸觀點中對西北的「西域」與「俄屬中亞」之視域與語言差別,正可代換為「藍色樂章」與「先民船舶」之海上移動時經由回望母體家園之視野中的回眸陸上世界之差別。[3]而海洋觀點中的「南方」,無論是東洋、西洋、南洋、東南亞,亦復如是。
[1] 魏源的《海國圖志》有60卷本、80卷本與百卷本,其成書固然受到林則徐《四州志》影響,同時兩人當面的唔談,也已成為學界研究魏源世界觀與海國觀時不可或缺的一次重要事件;然而,對於常州武進的李兆洛之輿地學、非漢非宋的經世學在魏源筆下的推崇,似仍為目前學界所忽略;尤其是以李兆洛為定點而上、下追溯其系譜時,可以發現魏源《海國圖志》中的「海國」與「圖志」之歷史脈絡的追索,決非如此單純,歷史洪流之下,仍有其它。其詳可參筆者所撰〈海上來的世界圖景---從利瑪竇到魏源〉(未刊稿)。
[2]杜維明,〈「文化中國」初探〉,《九十年代》月刊,1990年6月號。
[3] 筆者雖然從「洋」的視域以反思華人文化版圖之視野,這種傳統,早在司馬遷《史記》的《天官書》中就有了,由天與地,遂思居其間之人。但這並不表示海洋觀點是筆者之唯一。筆者所續思考的,尚在於一個母體文化在歷經近代的激盪後,其京畿觀與由此京畿而環中以塑之天下觀與歷史教育觀究竟當為何!無論是漢初的賈誼或是宋初的范仲淹,便不免令人生嚮,蓋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人物向文化獻言也。
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華人世界的文化版圖與視野 -- 近代第三華人世界論述
於
下午3:23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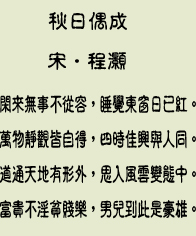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