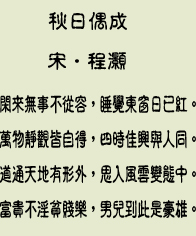中國歷史學會在台灣成立以來,迄今亦有數十載,想想它在當初成立之時,不但聚集臺灣歷史學界的精英,也聯同海外漢學界的華裔學者們一齊聚在此學會之下,凝成一股學界的力量,在大時代的動盪之中,延續了學術研究的命脈。這一回顧,乃是從學術的角度重新省視中國歷史學會的位置於今日,可得而言者,相信會引起許多會員的共鳴。這樣的觀點,同時也在證明一點,凡是真正的學者、真正有心從事治學問者,總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以及「歲寒然後知松柏」的,不管是在校園、課堂、還是書齋。正是此種讀書人的風骨精神,讀書種子遂得以續其命脈,在「師-生」授受中傳遞不絕,在「冷風熱血、一堂師友」中砥礪而勵,那怕是一線縷縷,也終將在「元亨利貞」的「貞下起元」之運會轉移中,迎來時代學統的風會骨氣,證成下一代的風嚮典範。
悠悠的時間與光陰,常在不知不覺中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生命階段還在當下,然卻每每總是於不知不覺中「俱往矣」都成了歷史憶往。當現在已被推移成其為歷史之時,必然總會想要伴隨著某些歲月深刻經歷所成就的生命深度,那一沙灘留痕駐足的一點渴望及奢求,是為了後浪來時能夠看到些甚麼,年輕的朝氣雖傲卻有理想、雖妄卻不假,這應當是回顧與懷念中國歷史學會的前輩時,想像他們必然是會如此期望下一代的。
今天,中國歷史學會便在這樣的轉折點上。憶往先賢、把握當下、迎來新血,這應當是一種無可如何的時間推移,正是在此推移中,時間雖然無可與之對抗,然而這偕流而逝的時間感受卻也給人在游向未來的同時,還可有一分可油然而興的擔當希望,特別是在這近一世紀、一甲子的編年運會的年代,不由得不讓人想起每個朝代都會醞釀出來的讀書人以及眾家讀書人薈萃出的士大夫扛鼎一朝江山的印象。
當年我的老師宋晞先生還在協助蔣復璁、趙鐵寒、方豪等先輩推動中國歷史學會的業務時,我還是一小孩子而已;一轉眼我成了博士生,擔任宋先生的助理,處理公務,當時宋先生已是中國歷史學會的理事長。那兩年宋理事長著實為歷史學會推動了不少有意義之事。與今日相照,中國歷史學會依然尚存有許多大老前輩,退而不休,風塵僕僕,想為歷史學界做些子事,這是前輩們的風範;也有許多中年學者,在成熟的學術根基之上,開始做些能做與想做的事,以為後來繼之的年青熱血者鋪出一坦坦的平台。這些都是我們能看到也能感受的的世間人生事,只要我們用心觀看與想看想感受的話。
歷史或史學這門學問自然「在歷史中」也有它自己的浮沈,不是每一個時代歷史學都是大熱門,就像現在!但世間亦往往有些子事,不是因為乘在風頭上熱門與否,才有其意義;往往在淡薄的年代,也才更能看出傳承的重要,與夫真能擔當傳承之認者有何人!在淡泊的治學之心靈中,可以看出邊陲治學努力的重要;而同時,要能看出邊陲其實是一種中心的不務正業、或是居於邊陲只是一個時代的學風想要轉型走上正道,臨此深淵之際,卻嘆找不到人來努力,往往也是歷史上常見的悲銘失寫!如果不想讓時代的中心軸流失了大本之學,流為迂腐之浮言,那麼,一個組織、一個單位、一個歷史人要做出的呼籲之言,大概也就僅止於此了!可進,則進;不當進,則退處書齋;有所為也,有所不為也;我們已感受到了。1911年迄今是一個已過一甲子而將屆一個世紀的編年;身為中國歷史學的理事長,面對另一個方將渡過一甲子的編年所紀,所進於言者,不在於《春秋》「正月」所書者為何所「統」,而更當在於史學應當與世道、與人心合繫於一事的「學有所本」!孟子之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凡人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以此來期許新一代中國歷史學會的成員會承擔的更好。
誠心祝禱中國歷史學會的每位會員都能身體安康,安康方能安然地活在當下,安然方能激發生命自生活當下向上提升一階,提筆書寫大史,儘從學問中來!
李紀祥 於2009年10月
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中國歷史學會第45屆年會理事長致詞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李紀祥教授主講“洙泗講堂”
——論孔子《春秋》之“書法”
9月2 9月25日晚,歷史·孔子文化學院2008洙泗講堂系列學術講座之二舉行,來自不同院系的百餘名師生彙聚“洙泗講堂”聆聽報告。臺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國際知名學者李紀祥教授,為大家作了一堂題為“論孔子《春秋》之‘書法’”的精彩講座。歷史·孔子文化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楊朝明教授主持了報告會。
李紀祥,1957年出生於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史學史、宋明理學史、清代學術史。主要著作有《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時間歷史敍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等。正式報告開始之前,李先生先以輕鬆的語言,愉快地侃談了自己與祖國大陸的淵源,和幾十年的“神州夢”,從而拉近了兩岸師生之間的距離;以詼諧幽默的風格,概說了孔子思想中“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以及師生之間“擬血緣性”關係的內涵,並對儒家文化及其發源地曲阜作出了全新的定位,即曲阜應不應處於縣市層級,而應有一個更高的定位,這讓我們想起了葛劍雄先生關於建立“文化副都”和我們一直主張的將曲阜建為“文化特區”的設想。李先生以其求學的經歷和心得,諄諄教導學子要“兩眼盯住六經”,心無旁騖,才會有所成就。
講座中,李先生主要圍繞著:《春秋》是否為孔子所寫;如何正確理解《春秋》中“隱西元年春是第一條,哀公十四年是最後一條”;今人與古人之比較;孔子儒學的未來發展動向四個問題展開。分別得出:《春秋》即為孔子所作; “隱西元年春是第一條,哀公十四年是最後一條”的說法未必科學;今人未必強于古人,古人未必不如今人;孔子儒學要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前提下吸引世界來欣賞她的真實內在,要以勇於敞開胸懷的姿態走向世界等結論。並且,李先生以與同學交流探討的方式,對“秉筆直書”進行了全新的詮釋。
李先生的報告旁徵博引,內容豐富;見解深刻,論證精闢;幽默風趣,深入淺出。與會人員均受益匪淺,收穫頗豐。該場講座既是一堂蕩滌心靈的文化薰陶課,更是一次跨越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
2009年8月3日 星期一
聆聽經典的聲音
聆聽經典的聲音
--有關《傳習錄》的「閱讀」
李 紀 祥
一、《傳習錄》:文本的傳世形態
從王陽明生前到他逝世之後,陸續由王陽明的弟子們編纂而成的《傳習錄》,迄今已通行於世間四百多年之久,從某方面來說,這本書已經被許多人認為它是一部中國人所必讀的經典。錢穆先生曾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六祖壇經》《老子》《莊子》《近思錄》《傳習錄》列為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典,其中《近思錄》、《傳習錄》兩部書籍被選入,反映的是宋明新儒學(Sung-Ming Neo-Confucianism)在中國文化與思想領域的地位。《近思錄》由朱子與呂祖謙編纂,凝結了北宋時期四位思想家的文本與語錄;而《傳習錄》則由王陽明弟子所編纂,初刻本在陽明生前即已刊刻,編纂與刊刻的目的都是為了傳播王陽明的思想。
現在我們看到的《傳習錄》版本,也就是一般通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可以稱之為「定本」,這是在王陽明過世後才完成其演歷的版本,從王氏生前到其死後,初刻的本子從一卷本而逐漸向三卷本演變,參與的弟子包括了王陽明弟子徐愛、薛侃、陸澄、南大吉、錢德洪等人;從最早的抄本到初刻本、續刻本、合刻本、重編本,從一卷本到兩卷本、三卷本,《傳習錄》三卷本的成型,學者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定論,比較可能的年代是在明代嘉靖35年或是37年;當時王陽明已經過世。
在《傳習錄》的三卷中,其實有兩卷嚴格說不能算是「寫作」,而只能稱之為「紀錄」---一如《論語》那樣;雖然其經過流傳之後,已經以「文」的形態向我們傳遞訊息,這點迫使我們必須以「閱讀」的方式來對此書進行訊息的重組,從這點來說,《傳習錄》作為經典,與其他經由「作者寫作」而來的經典,在表象上並沒有甚麼不同;但實際上,經過「閱讀」的中介,「閱讀者」還必須進入本書那原初的場景:師生之間的對話場景,才算是真正的進入了「記錄性經典」所想要保存的世界;這也就是說,在「閱讀」之後,「閱讀者」還須要「聆聽」,才能「聽見」王門師弟對話的聲音。因此,這使得「閱讀」《傳習錄》有了一個極為特別的進路:這便是閱讀其聲音的傳達。如此,閱讀便不再是一般措詞意義上的視覺閱讀而已,而更是一種聆聽。
筆者認為,從《傳習錄》最早的版本---抄本形態來看,這本書從一問世就已經決定了它的性格:顯然是「紀錄」性格的,也就是以「文」來追記「言」的。一方面它要記錄的是當下的老師與學生之對話發聲的場景,沒有聲音就無所謂「記錄」;另一方面,最初的版本之所以是「抄本」,那是因為最初以《傳習錄》來命名書名的本子,就是從徐愛所記錄的本子而來的;徐愛既然將他從老師王陽明那裏所接受的「聲音」留下了「文」的「記錄」,而這樣的「記錄」又在王陽明生前就被稱之為《傳習錄》而傳抄於同門之中,這已經表示「傳抄」以及「抄本」作為王門經典的歷史已然在王陽明生前便已經出現了初步的「文本」---抄本型的;則這最初的一卷本《傳習錄》,意謂了《傳習錄》的問世與誕生,是「以文記言」的「記錄聲音」類型的,也意謂著比徐愛的「記言之文」還要早、還要根基的時空,便是:「聆聽對話的聲音」。換言之,「對話」發生在「紀錄」之前,「聲音」是此一經典的根基,而不是「文字」;但「文字」卻是《傳習錄》作為經典並且流傳的樣態。《傳習錄》是一本須要「閱讀」的「文字性」經典,既非「錄像文本」、也非「錄音文本」。
二、三卷本中的兩卷與一卷
三卷本的《傳習錄》,「卷上」與「卷下」都是屬於「紀錄」的性質,紀錄了王陽明與弟子們之間的論學對話,這裏面可以讓人產生聲音迴響於人物發言場景的想像。而「卷中」的部份,則是從王陽明與同時的學者、學生的親筆書信中取材,改編成為對話的體裁而彷彿「遠距離通信者」就是「近距離對話者」。
對於「卷中」而言,雖然王陽明的弟子,從南大吉到錢德洪,都把這些「書信」編成了「對話」的體裁,但實際上,「卷中」仍然是屬於標準意義上的書寫與閱讀,只是加上了對話的戲劇化效果,彷彿「編寫劇本」那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傳習錄》的編者想要加入一些由王陽明「親筆書寫」的資料作為此一經典文本的成份。將《傳習錄》由弟子的「編輯」改換裝扮,換裝成為可以冠上「王陽明」之名的作品,以便在當時宣揚王陽明對抗朱熹的思想,應當便是這一換裝舉動的真正目的。但是,一方面是加入王陽明親筆的文本之換裝,一方面卻又是為了配合原來的體例---這意謂了即使《王陽明全書》已經刊行,但是《傳習錄》的影響力還在,因此,有必要保留這一書的原來形式:也就是以「對話」為主的「記言」形態,於是,遂有將王陽明的親筆書信改編成了「對話體裁」的「改編舉措」。這樣的法其實有些奇特與奇怪,迄今尚未有學者提出質問:為何會如此?既要冠上王陽名之名的親筆「寫作」作品,又要「改編」此一作品成為「對話劇本」;那麼,究竟《傳習錄》的作品定位,是應當朝向「原初場景」的「言」作定位呢?還是要朝向以流傳為主的「文」作定位呢?我自己認為,這一問題實在不好回答,也是我自己給自己提出的一個「我的難題」!我個人認為,《傳習錄》的定位應當是「記言」的:換言之,它既是「言」的、也是「文」的;就「文」這一部分而言,我們應當由「閱讀」進入它的世界,就如同讀一部劇本或是歷史、小說中的對話情節一樣;就「言」這部分而言,我們則應當學會「聆聽」,學會傾聽經典中文字發出的「聲音」,宛如王陽明的親身再現,在與弟子們面對面的對話現場中,吐出教誨與指點的聲音。
參與過《傳習錄》編纂的王陽明學生南大吉在〈傳習錄序〉中曾提到了《錄》與「錄」的意義:
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天下者也。
第一個「錄」字顯然是指「書」而言,因此標點符號上應當作:《錄》;第二個「錄」字,則指得是一種動作,尤其是對現場式的「言」所作的「文」的「記錄」的動作。沒有「記錄」的動作,將「對話」或是「聲音」記錄下來轉換成為「文字」,也就不可能有「刻」的文本傳世與流傳!
三、由閱讀進入聆聽的經典
筆者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近思」之《錄》與「傳習」之《錄》〉,詳細討論了這兩部代表宋明理學的經典,尤其是兩部書的書名中各有一個看來相同的 “Lu(錄)”字,而看起來是相同的符號,意義指涉卻大不相同。近思錄是由朱子所編纂的北宋四位理學大儒的著作選編,因此朱子是一位親自參與的編者;但《傳習錄》卻是由王陽明的學生們陸續編纂而成,由王陽明學生作為編者的書卻歸到了王陽明的名下,彷彿王陽明便是一位作者。我們對於這兩部書的印象常常是與朱熹、王陽明聯繫在一起的原因便是來自於這樣的一種背景。因此,這兩部書的書名中的”Lu(錄)”字看起來雖然相同,但是意義的指涉卻是大不相同:一種是屬於閱讀的,閱讀朱子所選編的文字,來追求閱讀者的自得於內心;一種則是傾聽的,閱讀王陽明與其學生們的對話,從文字中去傾聽對話的發言聲音,也是要聆聽者得到內心的自得與感受。有意義的是:者兩部經典中的”Lu(錄)”字便剛好在書名的書寫與刊印流傳中見證了字己的存在屬性,也見證了宋明理學(Sung Ming Neo-Confucianism)中所顯示出的兩種教育類型。
筆者在求學時代,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某一個晚上,明月當空而皎潔,筆者忽然感受到歷史像一條長河,而古人們的聲音便透過這條長河而傳來,筆者當下能親切地感受到為我所閱讀的文字之中的先賢的聲音。我們都知道,夜晚我們所看到的銀河之中的每一顆星星之光,雖說是現在的光,但實際上卻是幾千萬光年以前的存在、也可以說它是由已經成為歷史的星星所傳來的光;如果我們能看到已經是過去的星星之光於現在,那麼,從傳世的文本之中,我們也能聆聽到古人被文字所轉錄下來的聲音!
2009年1月24日 星期六
北京講演
北京講演
和一位台灣歷史學教授的會晤
藍蓮花
2008年5月3日 昨天,朋友告訴我,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先生要來北京,有一個小範圍的講座。我喜歡歷史,也喜歡錢穆先生,於是興沖沖地趕到香格里拉飯店。
李教授大約四十七八歲,和體態偏臃腫的大陸學者相比,他顯得相當消瘦。頭髮有些花白,眼睛卻炯炯有神,還長著中年男子少見的長睫毛。李教授對近代史非常精通,可是一個小時的講座和我們跟他的交談,他幾乎沒談及自己任何一個觀點。這個大陸學者大異其趣,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確實是個「外來者」。
他談了很多自己的感受。比如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歷史這門學科在台灣也不是那麼受人待見的,因為它看起來「無用」。父母花了錢送他念書,念的人文專業將來卻不會「變」出很多的錢,他的父母直到他讀到博士才覺得欣慰。大學本科的時候,他父母本來是要他學會計的,他對會計不感興趣,於是兩門專業課故意考了零分,結果父母只好讓他換專業。這樣的魄力俺打心眼兒佩服,因為俺對父母的強迫行為,尚不敢這樣對抗。
李教授提出了很多問題,對這些問題,他從不下結論。比如,大陸的現代史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而台灣從1911年起,為什麼?為什麼要把近代史單獨從清史中拿出來?上一代人提到歷史時會強調中國曾被西方列強欺凌,因此我們要分發圖強,超過西方,實現大國崛起,這樣的想法從哪裡來的?有沒有另一種看待歷史的視角?我們該不該向下一代強調民族仇恨?東方文明一定比西方文明差嗎?東方一定要融入西方嗎?為什麼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所有人會關注死了多少人,而不會關注死了多少隻狗?
這一切問題,在我們這裡都有現成的答案。教科書會教我們一個答案,老師也會灌輸自稱正確的答案給我們;長大後,又有另一群人站出來說,以前我們受的教育都是愚民教育,那些答案全不對,於是我們又信了另一套答案。於是乎這兩派的人經常打架,都說自己是對的,都說對方是漢奸、賣國賊,或者資產階級的走狗。這種思維方式,被我的一位好友稱為「二極管」思維方式,非此即彼,而從不問這「此」和「彼」是哪裡來的。
講座之後,幾個記者朋友爭相提問題。有一個朋友問李教授,如何看大陸新左派、新自由主義派和新儒家之爭,如何看儒家的政治儒和倫理儒的不同?李教授反問道:自由主義是哪裡來的?中文的「自由主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同一個概念嗎?政治儒和倫理儒這種提法是從哪裡來的?政治和倫理古漢語裡都沒有這個意思。李教授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的反問,讓我對語言的嫁接、衍生、變異等問題產生了興趣。語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李先生提的「文化中國」概念一定會關注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傳統語言發生的演變,以及對中國思維方式產生的影響。而後者是最關鍵的。
我問的問題是,中國的官僚集權體制幾千年來都未走出王朝更替的、治亂循環的怪圈,這跟我們的文化有什麼關係?李教授的回答是在黑板上寫下一句話:視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我注意到,他寫字是從右往左,豎著寫的。
除李教授奇怪的講座方式外,他的謙卑、儒雅,良好的教養也是大陸學者中少見的。沒有大學者的倨傲,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大陸常有的而且影響到學界的等級風氣在我們的交流中完全沒有。他真誠地跟我們一次一次地握手,誇讚我們的問題提得很好。
忽然想起席間一位朋友提到的一句話,在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中間,文化似乎在他們身上發生了斷裂。文化,真是個很沉重,很複雜的詞。
廣西大學文傳學院講演
春秋中“闕文”及“不書”,“空白”裡的閱讀與人生
--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講座後記
李紀祥,臺灣佛光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學術專長為春秋谷梁學、宋明理學史、清代學術史。李先生也是臺灣大儒錢穆先生的博士,關門弟子,著述甚豐。這裡想與大家分享的是我與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的一次零距離接觸,從大師的講座裡,我所聽到的奇聞軼事與感受到的點滴收穫。
在院長的歡迎致辭以及贈送完客座教授的聘書後,李教授從自報家門開始,語速平緩,吐字清晰地開始了他的演講。但當說及他的恩師錢穆先生時,看得出來他是有些驕傲的,不過我想任何一個曾和錢穆先生這樣的大儒接觸過的人,都會驕傲地去回憶那一段時光的,更何況李教授是錢穆先生的親傳弟子?
這裡我只是想憑自己的記憶,試圖為大家補上李先生話語裡的“闕文”或者感受他語猶未盡裡的“不書”。為了便與敘述和讓讀者感同身受,在這裡使用第一人稱,既是李紀祥先生的敘述,也是我個人的解讀,若你能跳出閱讀的巢窠,去解讀我的空白的表述後面的“已書寫”,我想你會領悟得更多。
我想“偷”一張卷子
外界盛傳恩師錢穆先生失明前,看的最後一張卷子就是我的博士入學考試試卷,然後先生眼睛就失明了,這件事我心裡總是有些不安,雖然先生失明與看我的卷子自然是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可是想到先生在那樣高齡還來看我那非常不才的試卷,心內總是有些愧疚的。於是有一次我便問先生,那張卷子是不是真的是先生批閱的?先生笑笑說:“肯定不是的!”那時我才安下心來。後來,我便有一直有一個瘋狂的想法,那就是把那一張試卷偷出來留作紀念,但學校的保安措施很好,我一直未能得逞,也不可能得逞。(講到此時,李教授臉上滿是孩童般的天真,聽者也不禁莞爾)
陳水扁趕人,馬英九賠禮
現今臺北東吳大學校園的西南角,有一座幽雅的小樓,1967年恩師夫婦倆由香港遷居臺北後,便親自選址這裡作為自己的居所,並命名為“素書樓”,一直在這裡居住了23年之久。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就是當年的臺北市市長陳水扁“無故”命令先生在其96歲高齡,雙目已失明時遷出素書樓,師母與我們這些弟子都不敢跟告訴先生說是被趕了出來,都說是房子要裝修,所以暫時搬出來一下。先生很想念素書樓,每天都在問,我們什麼時候搬回去呢?在這樣的境況裡,先生很快去世了。後來的市長馬英九幾次上門向師母道歉,但師母都斷然拒絕了他的道歉,這件事情對於恩師夫婦有很大的傷害,師母永遠也不能原諒不管是這一屆,還是上一屆,代表這個政府的他們,對恩師的所作所為。
恩師錢穆的風範
先生當年給我們上課時,總是大家都在素書樓坐定了,師母便給各位弟子倒好茶,然後,先生慢慢地從樓梯上走下來了。先生走得很慢,我們也都仰望著先生慢慢走下來。當光影從窗外射入,照在先生儒雅從容的面容上,歷史仿佛在瞬間沉澱,時空也似乎在刹那凝滯,我那時心裡想,幾百年前的朱子講學時,便大概也不過是如此的風範吧。
關於分裂的符號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分裂的符號,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的以長江南北為界的分裂,延續到南宋時期,南方與北方“異族”之間,以長江分界的分庭抗禮,長江成為了一個分裂的符號和象徵,但我們可以體會這種分裂的符號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於在未來統一的期待。現在的臺灣海峽亦是一個分裂的符號,有人會很詫異一個在地理上並不能成其為如此重要的符號的一道海峽,怎麼會形成一個同一種族之間的分裂符號。但若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可以發現,這其實並不僅是同一種族間的分裂符號,而是兩種當年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或是不同的世界勢力之間的分裂。海峽,不過是一個分裂的符號而已,既然如此,我們便可以期待這種符號後面期待統一的敘述。
關於共匪與蔣匪
可能海峽兩岸其實都經過了那樣一段歲月。當年老師的書房,是一般不會讓人進去的,如果能被允許走進老師的書房,就被稱為“登堂入室”的弟子,那是一種信任,一種榮耀,為什麼呢?因為老師的書房裡會擺有很多當年被稱為“共匪”的很多書,那時候的禁忌是蠻深的,藏有這樣書籍的房間自然不會讓一般的人進去,免生事端,因此得以同意進入書房的人,便是老師相當信得過的人了。而據我所知,大陸這邊了一樣經過這樣一段歲月的,可是我想問大家一句,當你們在各種各樣的文字、影像裡讀到的這些已經沉澱了的歷史的衝突,把它們擺在今天下午這樣一個時空裡來重新解讀,有這樣的一個我坐在你們的面前,我們在同一個精神世界裡進行交流時,你們是願意去接受那遙不可及的衝突,還是願意和我進行一種平和的思想上的對話呢?這兩者,又到底哪一個更真實?
自殺的權利與苟活的勇氣
法國哲學家卡謬曾指出,唯一的哲學問題就是自殺,人是有權利自殺的,這是存在主義的唯一正確的解讀。中國也有類似的敘述和表達,中國人一直有這樣的傳統觀念,那就是身體髮膚受之于父母,當身體遭受不可忍受的殘害時,人應該選擇自殺,那是對父母的尊重,也體現了在生命觀上的一種尊貴高潔的哲學情懷,例如王國維選擇自沉於昆明湖。但有一個很奇妙的命題,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際,成一家之言”的理念擺在自殺天平另一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選擇?其實西方世界無法瞭解司馬遷在遭受常人不可忍受的苦痛時,到底是應該去實踐自殺的權利,還是應該去體驗苟活的勇氣呢?
不墜青雲之志
夫人是醫學博士,在臺灣,醫生是在律師前面,排名第一的職業,很受人尊敬。我是學歷史的,旁人看來這是一個養家糊口也是有些困難的專業。有一回夫人的老闆請客,請了我去,他早早地把家裡櫃子上的名酒全都搬走了,放了一櫃子的書進去,還專門帶我去看,問我怎麼樣?我是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的,因為他在我面前其實是自卑的,他只是想告訴我,他這裡也有書,他也想做文化人,或者他也想算是文化人,我只是笑而不語。在座的應該沒有學理工科的,我想說的是,其實理工科的人都是很笨的(眾笑),我原本想妻子至少可以幫著教教孩子,現在看來,我要教兩個兒子和一個妻子(再笑)。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表現自己的傲氣與傲骨呢?我們做學問,須不墜青雲之志(鼓掌)。
《春秋》中的“王元年二月”
《春秋》為什麼成其為《春秋》?《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是因為《春秋》第一條是“魯隱西元年王正月”,而第二條卻是“王三月”。(眾面面相覷)為什麼《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是因為《春秋》裡沒有王元年二月。為什麼沒有?是因為孔子沒有書寫。孔子為什麼沒有書寫?是因為他已經書寫過了,他的書寫就是“空白”,是沒有選擇。(繼續面面相覷)他為什麼不選擇?是因為他認為不需要選擇,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其為《春秋》。那麼到底有沒有王元年二月呢?有,也沒有。《春秋》的魯隱公王元年二月,大約應該是周平王五十九年六月,在春秋之外,隱西元年二月是存在的,是真實的,而《春秋》的文本裡面,是沒有的。海德格爾曾說:“在世界之中(Be in the world)”,意思是此外無它,它們共在一個世界之中,而這個世界之外卻尚有世界。你若在《春秋》中,便沒有“王二月”,因為你在它的世界中。
春秋中“闕文”及“不書”,“空白”裡的閱讀與人生
“闕文”與“不書”是《春秋》中“空白敘述”的兩種表現形態,前者系一種“待書寫”,後者則是指向“空白”的“已書寫”,而非“未書寫”。“闕文”語出《論語》,被孔子用來指稱史官、書寫與傳統的關係;“不書”則是出於三傳,用以解釋春秋中的賦義,與無形之文的“空白敘述”有關。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狀態是可以被解釋的,三傳後學則能在“不書”與“闕文”之間進行“空白”態,為“待書寫”或是“已書寫”的意義進行識知及轉換。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種書寫行動,在這種行動中,有一種“空白”意識之察覺,但卻設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一旦我們在《春秋》的上下文間提示出一種“空白敘述”時,“空白”也就與有形符號一樣,也是一種書寫符號,必須加以閱讀及解讀。
傾聽燃燒的書和等待閱讀的書
當錢謙益先生在絳雲樓的火焰中傾聽他所藏善本書燃燒的聲音時,他能根據不同的聲音,聽出哪一部是宋本,哪一部是元刻麼?那裡面有生命的呼喊麼?各個不同的版本的確是有不同的述說的,那便是人的“在”和文本的“不在”的意義解讀。版本當然是重要的,不同的版本便是不同的生命歷程與世界,作者會在其中一直“書寫”,也會一直有“不書寫”,我們需要關注的不但有書寫意識的邊界,也有書寫的本身,“空白”是其存在的基礎與更為寬泛的釋義。總有一部書,會閃耀著經過長久的時間而積累下來的內涵,閃耀著歷史的美,在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你去閱讀。